“2014武汉•第三届美术文献展:再现代”
“2014武汉·第三届美术文献展:再现代”
学术研讨会纪要
整理:刘凯羚 统稿:马文婷
时 间:2014年9月13日
地 点:湖北美术馆艺术交流中心
主 题: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
学术主持:冀少峰 湖北美术馆副馆长
与会嘉宾(以发言先后为序):
贾方舟 批评家、策展人
胡永芬 中国台湾独立策展人
徐 虹 中国美术馆研究员
皮道坚 著名艺术批评家
黄继苏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王端廷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罗 岗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吕新雨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鲍 栋 批评家、独立策展人
鲁明军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讲师
孙冬冬 《艺术界》杂志编辑、策展人
刘礼宾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所博士
李 旭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
殷双喜 《美术研究》杂志社社长
王璜生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孙振华 深圳雕塑院院长
鲁 虹 著名艺术批评家
吴 鸿 《艺术国际》总编
高 岭 批评家、策展人
唐克扬 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付晓东 《美术文献》执行主编
严舒黎 美术文献艺术中心学术主持
刘 明 美术文献艺术中心总监
傅中望 湖北美术馆馆长
冀少峰: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媒体朋友们,第三届美术文献展学术研讨会现在开始。由于嘉宾众多,就不再一一介绍了。中国有一个尊老的习惯,这次贾老师在神农架举行的中国行为艺术研讨会上表演了倒立,引起广泛关注,首先有请贾方舟老师发言。
贾方舟:前不久我因倒立成名,不知道是悲哀还是高兴?可见批评家的批评行为还有很多值得去思考,比如批评行为为什么不可以以一种受关注的方式呈现?
这个展览让我感慨的是当代艺术不断有新人加入,大佬们也在不断改变自己。有关当代艺术和体制的关系,我认为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只要有那些关注当代艺术的人主持美术馆,就可能使这个馆变成一个能够推动当代艺术发展的平台。当代艺术曾经不被官方认可潜伏于地下,现在当代艺术在不断的强大,迫使体制不得不反思他们的态度。同样是国家体制举办的展览,如果全国各个省都有美术馆能够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当代艺术,中国的青年当代艺术家就会有较为优越的条件来发展自己。
《美术文献》这个刊物经过了20年,积累了丰富的艺术资料,展览上提供了很多值得我们去回顾的事件。湖北80年代初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中心,经过一段沉寂以后,现在以湖北为中心的当代艺术家群体又回到了武汉这样一个重镇值得欣喜。
冀少峰:贾老师的发言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话题打开了,既谈到展览,也谈了当代艺术和体制的关系,同时也中肯地评价了美术文献20年的作用。其实作为一个美术馆在建构自己的展览的时候是要满足公众多元多样的文化需求的,既要有传统的,又有当代的,还要有国际交流的。
胡永芬:我主要对研讨会的主题在台湾艺术界是什么样的情形作一个报告。西方20世纪思想史最重要的争论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当代艺术差不多和后现代的时间大致相符。整个现代主义脉络里的核心价值是理想主义。台湾对于所谓的国际化大概从80年代、90年代以后与西方接轨,有一种越来越深的焦虑。最近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开始有一种新的讨论,面对西方当代的主要思想概念,年轻人提出了某些疑问,就是所谓的重返现代性,艺术家开始思考用什么方式学习。台湾现代主义时期的前辈艺术家对那个时代发生的历史事件内容做了非常细致深入的田野调查,通过这样的方式重新去理解现代主义在台湾的思想意义。开始反思我们要如何拒绝西方霸权和国际主流的价值概念,重新寻找一个在亚洲的文化脉络,在这个文化脉络里面有我们自己在地的主体性、或者在地的发言权。
徐虹:大陆对于国际化的认知背景和台湾是不一样的。台湾是被边缘化后反国际化,而我们是想获得大国话语权而反国际化。
今天这个展览的策划很到位。虽然有很多中国的元素,但展览的定位不完全是要“再中国化”,显然有中国元素和“再中国化”不是一个概念。对于作品的选择,我从来就有一个理想,就是讲求作品的质量。从此次展览的作品选择能看到中国现当代艺术的一种转向,有了自己的主见和定力,及艺术家在主体上的自觉。这种自觉现在不能用“中国化”或者是“国际化”来评价。
1985年开放以后原有的高压并没有完全去掉但有一些松动,在湖北发出了一些强音产生了美术思潮。除了装置艺术,有很多艺术作品所用的红色元素、民间艺术、水墨画都有新的形式呈现,想要批判的东西恰恰又要在那里宣扬。而在这次展览里我感觉到真正的转向,当代艺术家掌握了有力的话语权,可以非常清楚地通过当代艺术将所批判和所不喜欢的东西表达出来。
新一代的艺术家要面临是怎样在世界语境中使自己更有话语权,这样的话语权并不不需要把整个民族拿来做盾牌,是艺术家的生存经验、头脑和天赋起主要作用。
皮道坚:湖北在八五时期是新潮美术的一个震中、策源地,理论刊物《美术思潮》的影响也很大。
当代艺术和体制的问题是和很多问题交织在一起的。以前有一个说法就是当代艺术要有文化针对性,这显然是正确的。这次展览有很多作品你一下子看不出它的文化针对性是什么,但我觉得这恰恰是这些作品成熟的一个标志。我们以前只是讲要有立场,有观点,但不讲有思想,有智慧,而语言上的成熟,恰恰是需要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智慧。匆忙看了展览的作品感受非常丰富,比如杨国辛的录像作品,作品在艺术语言和传统元素的运用上都很新意。谈到体制与当代艺术的关系问题,体制里是把当代艺术当做洪水猛兽,我们以前也容易忽视作品自身的思想力量,很长一段时间当代艺术给人的印象就是惊世骇俗。这次展览提示了当代艺术的常态化,即当代艺术不要靠什么事件来显示自己的力量,而是用作品本身,用你的思想和智慧来创作和显示。
黄纪苏:上午看了展览颇有动人之处。第一位老师讲到了当代艺术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与中国社会与重要的版块之间的关系,我接着他的话说。当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调,大量的热钱涌进了艺术领域,对艺术家既是一件喜事也是考验和威胁。谈到收编,除了有权力的收编,市场是不是也有收编的可能性、危险性?
提到“再中国化”那“中国化”是什么样的中国?“再中国”是什么时期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观?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建设伟大的社会,如果办不到这一点,走向社会就会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价值观简单的模式重复。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是需要有社会批判的,今天我在这里看到了艺术的一种过渡形态,批判的同时我也看到有建构的东西,反映了中国从解构又建构的过程。
简单来说,“再中国化”背后需要有一个中国观,世界观,这实际上也是需要艺术家与广大的国民一起在解构、建构辨证运动过程中来完成的一个事业。
王端廷:这个展览反映了中国当下当代艺术的新成果及中国当代艺术的复杂性。展览的题目“再现代”与研讨会的题目“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概念涵盖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矛盾。从现代、后现代、当代重新回到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从西方化(去中国化)再回到中国化是一个空间概念。而“现代性”这个概念本来就是西方的,与中国文化精神是相违背的。现代性有许多内涵,比如意识形态层面,文化诉求文化价值层面。这两方面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是矛盾的,回到艺术自身,从艺术精神和艺术语言更能直接解释今天所要探讨的主题。
回顾八五新潮后中国当代艺术史可以发现艺术语言上的变化。80年代初对西方现代艺术、后现代主义的形式上的学习, 90年代开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造性语言,到今天相对自由的多元化局面。在当代装置艺术形式中中国艺术家使用的创作材料和艺术语言非常有民族特色,如农耕文明的产物木头、竹子、纸和植物纤维等材料。而西方的装置艺术则趋向于工业材料和新材料,或者最新的技术手段如声光电媒介。是不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当代艺术有一种中国化的倾向呢?从意识形态层面回到民族主义其实是一种倒退。艺术家个体的个性化还是最重要的,个性里面就已经包含了民族性。而现代性、现代主义艺术的本质强调的恰恰是个性和个体,强调表现自我和个人自由。
冀少峰:其实我们是希望建构一个中国观,而一个中国观究竟要建构什么样的社会,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罗岗: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实际上已经适应了西方所主导的那一套规则,使得把“现代”和“去中国化”对应,再把“再现代”和“再中国化”对应成为可能。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要把自己变成完全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中国的问题在于并没有达到高度现代的状况,我们是不是可以追求另一种不同于西方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现代?“再现代”不是一个线性的概念,从“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我们再来做“再现代”。文化多样性是没有办法用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来完全统摄的。中国还处在现代过程中,而不是达到了现代的顶点,不能简单的进入后现代。这里面交织起来的话题很多,重要的是要重新回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要选择什么样的现代道路的问题。
吕新雨:我不是当代艺术圈的人,但今天讨论的话题我们都不陌生。
第一,“去中国化与再中国化”的标题隐含了一个预设:只有传统中国才是中国。“去中国化”指的是中国西方化,“再中国化”就是说我们现在西方化了所以要再回到传统,好像只有传统的中国才是中国。那么近代100年中国的历史算什么,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是否要重新讨论?
第二,台湾策展人谈到的重返现代性,这与我们这个题目有一点对着。我们的题目是说要重返传统,要问什么是传统,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传统中国?我们就会发现重返现代性又是和在地本土性联在一起的,那么“现代性”和“去中国化”、“再中国化”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去理清?说到台湾的在地本土性,我们很容易敏感,是政治话题,是文化话题,也是一个艺术话题,现代性包含了非常严重的认同政治的问题,认同的政治恰恰是破碎的,在艺术传统体现中我们就失去了一个道统。第二个问题是来源于我们对个性自由的推崇,然而个体的自由怎么放大也无法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和宗教的神圣性相抗衡。这样的困境使得我们的当代艺术成了一个交叉路口,社会的、艺术的、体制的、民间的,所有的这些冲撞都在这里爆发。作为个体的艺术家很容易去迎合西方资本,对艺术家来说应思考如何在诱惑中找到艺术的位置。
冀少峰:吕新雨女士提出中国认同的问题,以及要求我们重新回到艺术本身,恰恰也回应了徐虹老师刚才提到的,当我们重新回到艺术的时候艺术作品的质量、力量有没有。我们提出传统的中国是2000多年的文明,革命的中国是1949年以后到1976年,1976年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邓式的中国,今天是“再现代的中国”,这也是此次展览主要梳理的。
鲍栋:“中国”的概念是随着中国现代性进程不断被建构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两个关键词“再中国化”和“再现代化”是同构的两个方面,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其中最关键的概念是“再”而不是“现代”或“中国”,在今天的讨论中有个词缺席了,就是“当代”。我们今天谈到现代和当代到底是什么关系,在我看来我们不断提出要去再现代、再中国,都是再历史化,我们要摆脱线性历史结构再去看待现在,这时候就是再的反观反思。
我一直把当代性理解为不断回到现代性的原初的发生点上去,破除好像已经被规定好的线性的时间观念。特别是在中国与西方相比在一个跑道上,实际上西方已经比我们多跑了一圈,即所谓的“现代化”。而今天所遭遇的问题恰恰是和西方共享的,这个时候中国是不是必须要完成西方的200年的现代化进程才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不管再中国,还是再现代,都是紧迫的当代性问题就是不断的反思固化的历史观,打断僵化的时间概念。所以今天的关键词应该是“再”是不断重新输出。
鲁明军:从2007年的卡塞尔文献展至今都在不断思考现代主义的问题。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审美形式,回到为艺术而艺术的方式。我觉得再现代应该是站在当代对于现代主义的一次重新认识,真正把这个问题明确是上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没有现代、古代、当代之分,很多现代主义作品认为就是当代的东西,好像我们重返现代主义,再现代也是失效的问题。
在现代主义整个概念的生成梳理背后有一个现代主义叙事,这种现代叙事整个线性的叙事背后有一种连续性,但这种连续性背后还有一个对抗性。今天的当代最大问题是这种线性叙事是不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重新去寻找敌人的启示,我们不可能回到现代主义的整体对抗,可能是个体的,而且这种敌人是不断处在变动中的,甚至这个敌人也是一个临时的敌人。
孙冬冬:关于个体的问题,皮道坚老师说到当代艺术的常态化,换个角度来讲可能约等于当代艺术的职业化。知识界的几位老师也提到中国的当代艺术更多表现在市场层面的问题。其实当代艺术还不能满足于只是进入到国家、政府的美术馆做展览,要更坚信在民间状态下依然保持当代艺术活力的必要性。提到媒介的多样性,我个人不赞成用这种方式来去讨论当代艺术的问题,媒介的声光电最多就是在体现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一定要反映到某种精神表达上,应该是个人世界观问题。当中国的国家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并没有输出我们一个值得信服的世界观,与其这样不如去相信个体。
刘礼宾:现在反复讨论现代性、后现代性、现代性的再认识、后现代性的再认识,不如做一个好的展览给大家看。
我在“旋构塔——2014中国青年艺术家推介展”开幕上说到一个事:如果现在还用一种二元的眼光看待所谓的民间和官方,是非常幼稚的一个态度。再延续中国当代艺术的前卫策略性,把当代艺术变成一种前卫的、国际市场的符号,是自己玩死自己的方法。
现在很多人都太悲观了,中国民族自信心严重丧失,一提到“传统”就觉得我们跟传统是无法连接的,我觉得真滑稽。和传统连接可能有另外一种形式,我现在也没有完全摸得到,但我觉得这种途径肯定存在,包括绘画、文字乃至于对于传统知识的激活,不仅是一种知识化的传承。
李旭:今天这个展览没有让我失望,唯一需要改进的可能是材料、灯光等硬件的改造,需要非常大的经费。
现成品介入艺术表达之后有一个概念出来,就是命名即创造,评论界对于概念词汇的努力也是如此。杜尚的启示是历久弥新,界定一个人是什么主义、什么流派的时候目的本身就很可疑,他是一个好艺术家就够了。
再中国化当前面临一定程度的困境,我们语词上说的中国化、本土化、传统化这些概念都在描述不同的东西。中国当代艺术这个词的自足性其实也有问题,很多中国艺术很当代,但是不中国,它发生在中国,没有一点中国的灵魂或者中国情感的表达方式,完全是西方的;还有一些是非常中国的艺术,但是一点都不当代。
涉及艺术和生活的问题,当代艺术经常让我感觉到很贫血。我们经常看到两种艺术,一种是出世的艺术,艺术家的理论好听但作品没有说服力。还有一种是入世的艺术,作品虽然源于生活但一看就让人失望。我始终觉得好的艺术理论、理念背后必定需要好作品支撑,我不相信一个没有好的艺术作品的国家会产生好的艺术理论家。这个展览在未来会呈现出它的历史意义。
杨小彦:《美术文献》做到今天这个程度,说明今天这个时代传播的力量最重要,至于要如何评价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就像吕新雨说的“认同的破碎”。
在今天中国依然还不能向世界输出令人信服的世界观的情况下,个体的自由创造最重要。我切身体会到也许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爱谈“国际化”。“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这个词还说明中国是一个概念不断循环的奇特国家。如果我们真的重视艺术,那么艺术家的个体自由创作最重要,概念本身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还是成果。
殷双喜:看完这个展览,短时间内,我的感想也很破碎。
美术文献这个展览延续了《美术思潮》的精神。我们总觉得《美术思潮》停刊后,湖北的美术思想就停了,但现在看来《美术文献》从编者到思路使得湖北保持了理论和文献的积累。任何一个思潮,思想先行,编辑与媒体的价值在这里充分实现了。今天二楼的七号展厅让我有一种开悟,策展人把这种波普的,世俗的,浅薄的,虚假的,虚幻的东西放到一起,主题就呈现出来了。
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仍然是绘画占主流,这种形态今天要不要反思?我这些年参加的国际当代艺术展,大部分还是知名画家,绘画在今天作为当代艺术的承载主体,它还有哪些价值和局限?我觉得可以反思。
有些艺术家拿很早的作品放进来,我觉得有些应付的意味。付晓东做的“后现代时刻”,这个分展场虽然怀旧的趣味很浓,但游离于主展场之外了。傅中望馆长痛下决心把电影院改造成一个大型的影像展厅,其专业水准在全国是没有的,这里可以发展成当代影像、动漫、视频的动态艺术空间的类型。
关于“中国化”真的不是三言两语能讨论的。我知道一个细节,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中国际新闻是第一版,边区新闻、中国新闻放在之后,但后来中央高层领导说边区要放在第一版,把国际新闻放在最后。那个时候“中国化”就已经开始了,“去中国化”大概是一个现象和某些人的愿望。
王璜生:这个展览,首先让我感动的是美术文献这个展厅,我们看到艺术家和杂志的关系,批评家和杂志的关系,他们在每个历史阶段所作出的一种工作和努力。
就整个展览来讲,在这里看到了他们很多新的作品、新的呈现。特别感兴趣的是影院的问题,可推动中国影像作品的制作。
这次文献展的题目是“再现代”,研讨会的题目是“去中国化和再中国化”,好像我们面对当代艺术的讨论和思考的时候总会面对一个现代性或者现代化的问题,第二个是面对中国化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政府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当代艺术和国际上的现代性问题、当代性问题之间的关系很难用三言两语去说的。我们自身流淌的中国式情怀自然而然的抒发才是创作的关键,引用别林斯基的一段文字:“我们不应该老是怕我们自己生出来的小孩是会变成一个卷头发、高鼻子、蓝眼睛的非俄罗斯人。”
对于官方化我们现在都很警惕,其实我们很多机构都是处在体制内,如果能够用自己的某种力量去做好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工作,也是很好的一件事,不是不可能。今天这个展览每件作品的制作、介绍与公众的交流沟通都非常好,总体上能做到这么认真,也是借助体制的力量去对当代艺术进行推动,同时使他们能够与公众发生一些关系,值得支持和赞美。
孙振华:我谈三点感想。第一,再现代的展览在湖北美术馆与美术文献联合起来做有一种重启的感觉。湖北过去有一些很好的文化资源、美术资源没能延续,这个展览给湖北当代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继续做下去的话会在中国当代艺术版块中占有重要位置。第二,这个展览有话题性,它的主题“再现代”也好,或者是“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也好,属于元问题是很难争出是非的,是一个选择问题。我们对再现代的解读,一种是未完成的现代性,这是站在西方立场来看的不管是谁都要去面对的;第二种解读是另类的现代性,现代性不仅是西方性、普遍性,我们可不可以做中国的现代性,地方化、地域性的,不同于普遍主义的现代性。说到最后又归结到元问题了,是可以永远争论的问题。第三,从这个展览中我看出策展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有一种艺术家不管你提出什么主题,他都这么画。还有一种是比较考虑到语境、考虑到策展人的口号。有些艺术家喜欢读书,偏理性,始终想要占在最新的前沿;还有一些艺术家永远凭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感性在创作。一个艺术家读书当然很好,但最重要的是要更感性地投入到当下的生活,注意此刻生活给你的切身感受,不然再多作品都是拾人牙慧。
鲁虹:整个展览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残缺的文献”这个单元,很多当年的情形都展现在脑海中。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对中国当代艺术从发生到现在是很难全面概括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艺术家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超越文革的极左模式,进而创造有现代意义的新艺术。普遍的想法就是借西方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手法,但因为其观念资源、视觉资源都是来自于西方,所以带来了去中国化问题。“去中国化”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的是去掉了文革中的极左模式或传统中的消极元素,坏的是中国传统里面好的元素也被反掉了。
到了80年代末期很多艺术家也注重把中国自身传统文化元素吸收进来,如徐冰的“天书”,傅中望的“榫卯”都表明他们既注重向西方学习,又注重吸收中国传统元素。“再中国化”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中国辛亥革命以前的文化传统中去。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在这个过程中结合中国的现实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使西方当代艺术的很多元素中国化,然后把自身传统元素当代化。
吴鸿:本次展览主题叫“再现代”,我开始的理解是回到现代或者是回到八五新潮时期,现在看到研讨会的主题是另外一种形式,按照A到B,B到C,C不同于B,回到A就和A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又不同。这是辨证法式的解释,研讨会的主题“再中国化”是对于展览的主题“再现代”的一种补充,是第二种对“在现代”的解释。
这个展览提供给我们观察和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现状的非常好的机会或者是一个案例,但里面缺乏一些活力,不是策展人的事情,而是目前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今天的很多作品制作固然精良,艺术表达语言也更有艺术性,但是它的内核、精神和价值观是越来越被稀释掉了。
高岭:第一,对于这个展览的第一印象就是关于规模、形制和作品本身,这是近一两年比较值得称道的一个展览。第二,研讨会的主题。我赞同李旭命名即创造的话题。我们干评论的自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我们就是搞命名的,文字工作就是玩概念。立言正名,就是要名分,给艺术家名分,给自己一个说话的名分。
关于“去中国化”和“再中国化”的问题,知识界讨论了20多年难有定论。我建议研讨会的题目尽量鲜活和视觉化,讨论起来更有针对性,大而空的概念,不是美术界的强项,我们不妨把它交给知识界。年底湖北美术馆创办的论坛,题目就是美术界所专有的一个语言表述方式“展陈与观看”,这就是美术馆在当下的功能和意义。对于同样是用文字语言、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人也容易上手,艺术家也容易进入,观众也容易参与。
冀少峰:谢谢高岭老师,说不清楚和说得清楚的问题要同时存在,宏观和微观的也要同时存在。下面有请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唐克扬发言。
唐克扬:展览的题目“再现代”本质上是时间的命题,研讨会的题目“去中国化和再中国化”本质上是空间的命题,似乎没办法放在一起谈,但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一直是在转化之中的。就拿武汉来说,就存在时空悖论。武汉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分水岭和重镇,一方面并非沿海城市,不应该是得风气之先,但同时在中国现代艺术的历史上,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一直起到了领军作用,可以说既厚重又活跃,这是很好玩的一个事情。
美术馆也同时包含着两种并列的矛盾要素:一种是关于时间,一种是关于空间的。我们把美术馆也叫做艺术空间,但每个展览同时又无时无刻不是一种线性的叙事,带你进入一种时间的河流。展览本身也是这样一种时间和空间的互相转化。作为一个美术行业的从业者,我们应该着眼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尤其是转化过程中是什么样“个人的”时间变化产生新的空间,什么样“在地的”新空间带来新的时间观念。进入到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改变中,这些问题可能会得到更有趣的答案。
付晓东:非常感谢湖北美术馆和美术文献艺术中心邀请我来做这次展览的单元策展人。在“刻奇博物馆”这个单元,我试图从中国现实情况里面去找到一种新的美学可能性,这些艺术家并不太关心最时髦的西方理论,而是非常关注当下的生活体验,以及他们目之所及的现在的城市和城乡结合部、生活周围的环境所产生的视觉和体验上的审美经验,并试图把这些归纳出来,组合在一起,建立自己的一个审美系统,以一个博物馆的方式来呈现。我之所以做这种低级的美学经验,是希望能够在像武汉这样一个市民文化的城市,发现日常的美好的东西可以进美术馆,可以被转化成为高级趣味、高级美学,完成从低级向高级的颠覆。“后传统时刻”和“刻奇博物馆”谈的都是一回事,都是边远的传统文化对正统、中心、压倒式的现代性文化新的可能性的反驳。
严舒黎:我先说一下“残缺的文献”这个单元作为美术文献展的一个线索和背景,包括了美术文献展的创立、延续,也承载了创立者所具有的对当代艺术的热情。
关于“现代性”,是在哲学界、美学界、文学界讨论得非常多的问题,艺术界讨论这个问题就需要有独特的地方,我个人觉得付晓东两个单元也是对现代性这个大话题作出的一个比较具体的阐释。
我们做这个展览就像讨论现代性一样讨论所谓的东方、西方、官方、民间等这些二元对立的东西。美术文献艺术中心和湖北美术馆处于不同的系统、不同的体制,这种跨界的对话也是希望能够打开我们的思想。在短时间里形成这么一个展览,是多方协调、妥协、拉力的过程,最后呈现出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景观。我觉得比起强调大技术、大规模的展览,细微的东西更有意思,宏观的和微观的都需要。中国梦是现在提到很多的话题,如何把中国梦变成一个美梦而不是恶梦,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态度和价值。
刘明:美术文献展是一个从本土出发,有它个性的展览。在目前这样一个体制和湖北艺术生态环境下,要做一个高水准的三年展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从美术思潮到美术文献,再到文献展,当初的创办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把调门提得很高。我们从第一届到现在的第三届,每届都有很多问题要去解决。这一次也感谢湖北美术馆和傅中望馆长,我们双方要利用资源和优势让这个展览有持续的保障,健康地延续,还请大家继续关注,我相信第四届、第五届做下去会是一个更有水准的展览。
冀少峰: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涉及到很多方面,大概归类一下,比如谈到了艺术与体制的问题,重返现代性,主体性和在地的发言权,以及国际化和国际接轨的焦虑。有老师提出来要注重展览当中作品的质量,要强调艺术家的精神,展览的话题性等问题,同时还要建构中国观,要建构一个中国的融入世界的,推出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也有学者提出中国认同和认同破碎,“破碎”成了我们今天研讨会的热议词。还有老师提出双年展的体制和策展人的关系、当代艺术职业化、以及我们也提出了为什么如此热衷国际化、全球化。也有老师提出艺术家与策展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批评家提出的艺术的活力等问题。另外,彭德先生因为有事情不能到场,特撰此文发来。
彭 德:一件艺术作品进入历史、变成公共记忆,有五个通道。艺术作品转化为照片、影像、印刷图像和数字图像等文本,用于传播,是进入历史文献的第一通道。作品参加艺术展览,接受艺术圈内外人士的审视,是进入历史文献的第二通道。作品被批评家评论,变成人们鉴赏和议论的进口,进而形成跨专业的舆论,是第三通道。作品被拍卖、购藏、转卖,在世上流通,经常引起关注,是第四通道。作品被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机构永久收藏和陈列,是第五通道,也是最具专业影响的通道。
一件作品即便具有上述五个自身价值之外的通道,也不能保证它能穿透现实和历史。作品自身的穿透力量,在于它属于这个时代,代表这个时代,甚至能唤醒这个时代。它能扣动这个时代的神经,表达这个时代世俗的或精英们的意愿,让人心动,或者愉悦,或者震惊,或者激愤,进而启发人的感受,引发思考,以致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具有普世的和长久的感染力。
美术作品的文献价值,还在于它的作者。一件有魅力的作品配上一位有魅力的作者,曾经是和永远是作品传世、被人不断言说的艺术佳话。两者如果都能在高端的位置和大范围的平台,形成相互支撑的关系,作品就能成为时代的标杆和永不消失的文献。(注:作者未到场。此处为其撰写的发言稿,发表时有删减。)
傅中望:湖北美术馆经过七年的运行,不断在进行文化的创新,我们在跟上级机构谈到三年展的时候,其实他们对当代艺术,对带有前卫性的、甚至还有一些批判性的作品还没有这方面的认知。从推动湖北美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湖北美术馆在当代艺术有两块品牌:一个是三年展,一个是三官殿一号展。我们湖北美术馆没有深厚的传统积累,唯一就是重新选择和创造,通过展览收藏作品。通过这种不断推动的方式让湖北美术馆的展览、收藏、研究、公共教育全面地提升。从办馆的角度来说,我们必须以多样化的多种的艺术方式来满足公众不同的精神需求。
今天这个展览对于湖北美术馆无论是从观众的角度,还是从学术发展方向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特别是今天各位专家也提到我们开辟了新的影像馆,其实这也是公众的需求。我相信通过这个展览对我们的观众,特别是对学院的艺术教育和当代艺术创作,以及对年轻艺术家们都会有很好的影响。
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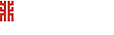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