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影像:光的实验场——2015三官殿1号艺术展”研讨会
“再影像:光的实验场——2015三官殿1号艺术展”研讨会嘉宾合影
研讨会纪要
整理:卢嘉一、陈雅洁 统稿:卢嘉一
时 间:2015年12月18日(星期五)下午14:00 - 17:00
地 点:湖北美术馆四楼艺术交流中心
主 题:光的实验场:数字时代影像的语言探索
学术主持:冀少峰(湖北美术馆副馆长、展览策展人)
杨小彦(展览策展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与会嘉宾(以发言先后为序):
顾 铮 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
郭力昕 媒体评论、学者
刘 洁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纪录片研究者
李 波 《中国摄影》杂志副主编
殷双喜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研究》主编
孙振华 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深圳雕塑院院长
刘 淳 《黄河》杂志社社长、批评家、策展人
鲁 虹 合美术馆执行馆长
王端廷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段 君 北京理工大学美术学院教师、青年批评家
胡 斌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
赵洪生 邯郸学院美术系副主任
娄 宇 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刘 钢 策展人
谢 慕 雅昌艺术网执行主编
徐 亮 《世界艺术》主编
李裕君 《绝对艺术》总编
郑梓煜 南方都市报高级编辑、展览策展人
杨小彦:经过一年的筹备,“再影像:光的实验场——2015三官殿1号艺术展”在湖北美术馆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如期举行。
这个展览之所以叫“光的实验场”,是因为在筹划过程中,几位策展人在讨论和选择作品时很明确地意识到所针对的对象是“光”,“光”既是手段也是对象。在这次展览作品的选择上,既有对影像的深入探讨,也有以影像为表达手段来寻求新的可能性的创造,同时,还有利用现成图像进行合成篡改或叠加,从而生成新的意义的尝试。这些作品并不局限于狭隘的摄影、数字成像、电脑艺术,我们想给它更大的包容性,我们试图通过艺术家及作品来展示数字时代影像各种可能的发展状况。
今天的研讨会邀请有批评家,影像、传媒领域的著名学者、艺术家,首先有请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顾铮教授发言。
顾铮:当代摄影、录像艺术在丰富多彩的语言和观念上所做的尝试,对我的关于影像的一些固定观念来说是一次冲击。湖北美术馆影像展厅在国内美术馆中时唯一的,这是其对当代艺术的一种理解和定义,从空间上提供和创造了条件。听杨小彦说“再影像”,我第一反应“再”是“Re”,今天看到海报“再”是“beyond”,中国人把“beyond”翻译为别样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这也是一种理解。
现当代艺术无论从叙事或题材内容来说,具体性经常是被解构、颠覆掉的对象。而无论是历史影像、符号化实验还是现实,总是有一种对应关系。今天的数字时代影像更趋向某种抽象化的或者高于现实的转换,包括叙事上的挑战。影像的力量何在?我们想要把影像分解掉,或是转换成一种抽象的、高于现实的,或者是对历史、现实作出一种更具精神性的解读,但影像一定要把我们拉回到某种和我们经验匹配的现实中,即使它是被解构了的。
这就回到我对影像的基本认识和判断。今天的展品很多大家都不需要看懂,只是对现实重新组织了一次叙事描述。杨小彦实现了他的构想,这几十年来影像对我们的栽培、滋养、毒害,到今天要靠这样的展览彻底重新丰富和颠覆,这就是“Beyond”。这种超越某种意义上就是超越自身,超越现实,接下来可能是一个很自然的影像的超越。
杨小彦:在当代艺术领域,我常常发现在我解释完一个作品后我自己很清楚,但听的人并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郭力昕:我是学新闻纪实摄影的,从创作到评论,过去几十年来被纪实性、现实等关系所捆绑。再接触当代艺术,不管是摄影还是录影艺术,或者有实验性格的纪录片,在这些艺术家丰富多元不断再创造的作品中打开自己的一些想象和影像的可能性。中国大陆的视觉艺术和当代摄影过去二十年中在质和量上不断丰富,群体创作力旺盛,其中的想象力、话语能力都非常令人惊讶,爆发力很强。
关于影像和现实的关系,最近看到1983年约翰伯杰与苏珊桑塔格的对话,约翰伯杰强调小说必须基于现实进行想象来说故事,而桑塔格说他作为摄影批评者和理论论述者,是贴近现实的,当他成为一个小说家时他可以完全进入到一个想象的空间里,并不需要以现实为基础,他认为文字和文学可以开发我们想象的可能性。桑塔格不是一个不关切现实的人,对国际政治、对美国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但他提醒我们艺术的修辞和艺术语汇上的创造性、虚构性,如果能够对这个美学本身很纯粹地开发,他认为这有助于我们迂回地回到现实,现实也许会被描述得更加深刻。
回到“再影像”展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较现实的符号,也有一些相当好的艺术性的处理,有些看起来很直接。然而“再影像”的主题是“光”,它本身就不止是一个媒介。在这样的思考下,彻底地解放对艺术的可能性,它终究还是可以反馈到对现实的描述和反思。
刘洁:我在传媒大学一直研究纪录片。中国纪录片的现状是除了主流媒体的宣教、歌赞式的,商业性的,同时还有一大批不被认可但是在国际电影节上非常活跃的独立影像,他们的作品通常用纪实的方式发出抗争的呐喊与思考。此外,纪录片节还有很多原本学艺术,后来拍影像的人,他们游走在纪录片界和艺术界之间,产生大量表现诗意、情绪的纪录片。
中国纪录片受欧美影响很大,一是反映现实的,二是反映思辨、思想的,包括歌赞式的专题片,三是游走在艺术实验与纪录片之间的诗意化影像。刚在展厅中看到丁澄导演的纪录片《聆听澳门》,把声音形象化,把形象音响化,在澳门古老的叫卖声中,我们看到历史是从当下的纪实走进去的,它和纪录片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从这个角度讲,这不是跨界,而是混搭。现在世界上没有创新,所谓的创新是混同起来的。展厅中还有一些图片,把原来认为属于艺术与建筑的界限也破除了,甚至将艺术的表意和纪实混同在一起,尽管这可能对普通观众来说存在一定的解读问题,但最起码这是创作者通过他的思考、情绪选取他认为最合适表达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正如一位俄罗斯艺术家所说:“通过思想所呈现出来的形象,比思想本身更重要。”今天会议的意义也在于混同出创新。
李波:这个展览邀请了一批中国最活跃的当代影像艺术家,让我看到了当下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创作状态。各位老师的发言都不约而同提到一个问题:摄影与现实的关系。光对摄影来说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还具有物理性。无论是传统银盐还是数字时代的像素,通过有光才产生了摄影和影像,不管通过什么迂回曲折的路径,影像的产生还是在确认现实,确认拍摄者的在场。
这个展览打破了传统摄影中用影像记录、还原现实的单向度关系,策展人、艺术家把影像如何生产、传播、被观看,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都展现在我们眼前,形成了数字时代的现实本身。
殷双喜: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叫“数字时代影像的语言探索”。影像是一个比较新的艺术媒介,当下已经成为大型展览的标配,但从摄影技术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一个传统媒介。在看了许多展览后,我的体会是很多时候对影像的观看体验就是穿梭在一个个展厅中的黑屋子里,看一个影像超过两分钟还无法理解其含义,就前往下一个黑屋子。然而,在所有人都能通过手机等媒介很方便的生产照片或影像的今天,如果影像不是一目了然,它的存在还有何价值?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讲摄影艺术,这个艺术有何所指?是艺术处理手段还是艺术观念、思维?这个问题各行各业都遇到过,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一旦交融,就会发现在大众文化的海洋中想要突出自己很困难。
影像诞生之初是作为绘画的替代,缩短了绘画时间。它的曝光从最初的几天、几十个小时,到今天的几千万分之一秒,成像速度越来越快,解决了再现能力之后,就需要在此基础上索要一些东西。影像是一种连续性的时间性观看,和绘画独幅的古典式玩味不同,貌似简单,容易成像,但涉及现实和真实两个概念时还是非常有力、有价值的。
今天展览中王宁德、王国锋等艺术家的很多作品,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不可替代。任何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如果让人感到不可替代,那么他的价值就存在了。反之,如果一个展览把影像作品标签都去掉,任何一个人都能拍出相应水准的影像,那就要考虑到作为摄影家的独特性和价值何在。器材的改进是无止尽的,技术性的东西也可以分化代劳,而把这些都过滤掉之后,才是影像艺术家特殊的自身价值所在。
孙振华:今天的展览基本可以对中国影像艺术现状做一个全景式鸟瞰。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装置、行为和影像比较有相似性,常常因为被冠以“观念”二字来进行修饰,而忽略了其中的技术性问题,使得这三种艺术形式在当代艺术中虽然很前沿,但也越来越标配化、标签化了。
展厅中的作品有摄影、纪录片等,它们之间还是有方法论上的区别,有的作品试图在现实和自己的呈现中找到一种对应关系,更多的是一种观念性,还有的带有社会伦理的关怀,也有一些属于纯本体的,研究摄影本身。面对这样纷杂的影像世界,最重要的是要看它背后的观念及时建立在什么样的方法论基础上进行自己的创作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展览中很多作品的确不错,如王宁德、冯原、王庆松等,他们在不同的方法论上,彼此差别很大,这也是这次展览有意思的地方,为每一个研究在和评说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今天谁也不敢说影像不是艺术,但它早已不再是起初的单纯对写实性绘画产生威胁,甚至还有一点自我放逐,放弃和现实的直接对应。影像作品在展厅中,似乎很少有人能从头看到尾。特别是观念性较强的作品,甚至会让观看者产生疯狂的感觉。在美术馆有限的空间中面对这么多影像作品,如何保证它传播的有效性?影像离开美术馆空间怎么办?还有它将来的方向,能走多远,这都是问题。
刘淳:80年代初读书时和老师讨论,认为摄影不是艺术,这个情况在今天发生了很大改变。1949年以后,中国摄影的存在和发展几乎完全依赖于意识形态或被意识形态所控制,是宣传的工具和政治的附庸。改革开放后摄影成为思想解放的载体,成为一种警示的力量和普世价值观,抛弃了个人感性和体悟的融入,放弃了摄影的语言、修辞、技术和形式的展示,由此展现了观念摄影的思想、立场。换句话说,拍什么可能成为观念摄影的重要选择和方式,这种新艺术现象与通常意义上的摄影几乎毫不相干,是两种文化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观念摄影出现了非常活跃的局面,这种局面几乎是在当代艺术的范围内展开的。观念摄影打破了关于摄影的传统定义,使原有摄影标准得以改变,证明了其为一种极其自由的媒介,也意味着摄影价值标准多元化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更重要的是摄影工作者认识到摄影可以是目的和手段两全的表现媒介,观念摄影会引起人们对摄影本身的关注。我们期待在当代艺术健康发展和成长过程中摄影再次发生新的变化,而观念摄影也不再是在当代艺术中产生影响的艺术现象,而是一个可以在广义摄影界产生影响的表现形式。
鲁虹:这次展览中有些录像作品很不错,如杨国辛的《拓》,用特写方式拍摄手拓古碑,配上巨大声响,很感人。还有好几个艺术家用了摄影手段表达观念,很适合展出,也是架上绘画无法取代的。如冯原的作品表达了早期的文化逻辑,一方面要有中国元素,一方面又要有世界性,这种文化逻辑一直在延续。王庆松的作品,体现出对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深刻反思。王国锋的作品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建筑,像罗马尼亚人民宫,突出了权力的欲望,这不是绘画能够取代的。还有翁奋的作品也很有冲击力,多年来一直对中国飞速发展的、病态的城市化建设做反思,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影像艺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媒体,多有当代艺术展览几乎都有影像作品。影像是一种时间艺术,放映至少需要一分钟以上,这使其在展览中展示效果非常不好,很少有观众认真看完展厅中所有影像作品,所以我每次做展览基本将录像控制在四台以下。我并不是看扁影像艺术,而是认为影像艺术需要很好的研究一下如何从传播的角度解决现存问题。
王端廷:数字成像时代是一个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时代,这也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观念自然延续的结果。这个时代技术已经不是问题,衡量艺术作品价值高低主要取决于艺术家的创意和思想深度。
当代影像相对于传统在功能上发生很大变化,可以是形式主义艺术,也可以是纪实再现性艺术,还可以是观念艺术。从艺术语言角度来看,可以分为纪实再现、表演摆拍、现成图像挪用和再造、虚拟等形式,这也使得当代摄影和影像艺术领域出现了两种艺术家,一种是摄影、摄像师,一种是导演型的影像艺术家。现在很多摄影和影像艺术家自己并不操作照相机和摄影机,只是提供创意,这也是当代摄影和影像艺术的一个新现象。
刚才殷双喜和鲁虹一再提到一个问题,很多观众没有耐心观看影像艺术,但是影像艺术在当代艺术展中又不可缺少。数字摄影和影像何以有效并受追捧,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任何手段都是因为需要而产生的,在人类艺术史上只要有一种新的观念,人们就会创造一种语言来表达这种观念。数字摄影和传统摄影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呈现的都是形象在时间中的切片,但在呈现图像的急速变化的速率上还是有很大区别。数字摄影和数字影像艺术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它们与当今日新月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与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是相匹配和相对应。
我们看当代影像作品要看整体才能理解它的意义。艺术家需要一定的时间量来呈现形象或场景,这样一个作品才能具有与传统艺术同样的价值。这也要求观众有一种相应的态度和相应时间来接受它,就像我们不能用看绘画的方式来看电视剧和电影,对于影像艺术需要抱有一个新的态度。
段君:80年代末期或者是90年代中后期,得益于前卫的纪实摄影和中后期的观念摄影,当代艺术界讨论摄影与摄影界理论的融合度非常高,但从90年代末期到今天渐渐产生隔膜。一方面,当代艺术理论界可能倾向于将影像视为当代艺术的一部分,或在这个框架内研究摄影。另一方面,摄影理论界觉得摄影有其本身的特殊性,是有媒介语言的本体。其实,这两个方面还是有区别的,我个人认为影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摄影和录像是两回事。
这次展览主题的“光”作为摄影核心元素,最主要的作用是引起观看与观念的关系讨论。展厅中的作品不完全集中在光对于摄影或影像画面的塑造,而是经由技术或语言,包含了各种客观因素和艺术家主观的创作情感。杨小彦为展览写的文章中还提到冷媒介和热媒介,这是关于影像本体的研究。在摄影作品中语言和题材分裂的情况非常严重,而杨小彦老师把摄影理论和当代艺术理论重新连接,在当代艺术理论界有效的讨论摄影和录像。他的策展前言阐述了用传统艺术理论讨论今天的影像失效的原因,并通过展览的案例和理论本身的解释解决这个问题。
我还有两个看法,第一,展览虽然以光为主题,但很多摄影和光完全没有关系。从策展的角度看,如果集中展现中国当代摄影或者是当代录像对光的表现,多一些有语言、内容和艺术家情感的光的作品可能更好。第二,蔡凯先生的作品模拟游泳池的水面的光感,从艺术家创作的线索来看,他之前的创作擅长对光线的切割,如果把这件作品放入展览整体框架中,除了幻觉、真实和虚拟的关系之外是否还有更深的层面。
杨小彦:视觉理论和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影像、图像、视像这些名词很难对应。“光”作为造型手段是隐形的,录像、摄影必须拍在光线照射下的物体,我们看到的是物体,光是造型。对于王宁德来讲,光已经走出来成了对象。我不断考虑究竟摄影重要,还是对象重要。
胡斌:展览题目“光的实验场”和“再影像”展开了两个轴线:
第一, “光”不仅是造型手段,还可以作为一种精神性的象征。如展览中蒋志的作品,光线光照形成某种古典效果的画面,被他改造成了由线牵扯出的一种带有肉体的刺痛紧张的感觉,这里面有某种肉身的经验和精神性在里面。
第二,“再影像”中的“再”是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我们用新的角度来看影像,一是影像的新阶段。今天的展览将动画、电影、纪录片等动态影像和摄影(静止的图像)一起放入同一个框架下,是对影像艺术发展中错综复杂关系的一种直观反映。不仅打破影像内部界限,也将学科之间的界限,和学者、艺术家和策展人之间的身份界限打破,重新看影像,这些都是“再”的意义。
关于影像的新阶段,我谈一下虚拟。现在有一个词叫“后网络”,不完全是纯粹的虚拟的世界、虚拟的艺术,而是通过艺术家有意地把虚拟和现实的界限进一步被打破,使现实和虚拟、公共和私人的空间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杨小彦:“再影像”和虚拟之间可能没有绝对的边界。
赵洪生:上个世纪以来,传统造型艺术的地位收到很大挑战,影像艺术进入当代艺术领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创作艺术作品的新媒材也不断更新,新媒体技术的出现,给艺术家的观念、创作形式带来很大改观。
第一,展览体现出了一种实验性和前卫性,借助各种媒材来表现和实现自己对人性、本质、自然以及历史、传统等等各个方面的思考。同时,把前卫性和媒介的特性融合在一起。
第二,大众性和平民性,摄影艺术发展到今天,能够实现广泛的民众参与程度,使影像艺术的公共性更加突出。
第三,当代数字艺术、虚拟艺术的互动性和观众的参与性,以及交互性。观众的参与可以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是当代影像艺术一个突出的特点。
新媒介手段代表的新艺术将改变观者的观念,在图像泛滥、瞬息万变的今天,艺术家会从中选择什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这是我思考的问题。
娄宇:第一,近年来看到很多影像作品,但对我吸引力不是很大。我认为“光的实验场”同时也是一个对话和互动的实验场,未来影像艺术的发展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有社会效应的艺术形式,值得我们思考。第二,对展览的释义。“再”字是重复、颠覆,还是一种超越?我认为应该体现其前卫性、包容性和实验性。在今天的泛图像时代影像艺术可以成为最大众化的艺术,但反而成为小众,甚至在从事专业美术史研究或批评的人来看都很难融入进去。
影像艺术是后现代语境中的一个概念,分为“前影像艺术”阶段、“影像艺术”阶段、“再(后)影像”阶段。第一阶段从照相术产生到上世纪60年代,第二阶段以白南准1963年德国影像艺术个展为标志,第三个阶段从21世纪以后,特别是从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技术及网络技术发展之后。影像艺术本身涵盖多元手段,与行为、装置形成互相捆绑的关系。虽然近年来还开设了相关课程,但大多数人对“再影像”本身的认识依然十分模糊,理论和批评的滞后也是造成这种尴尬的原因之一。今天的研讨会本身也是对中国当代影像艺术的一次集中梳理和对话,在这样的实验和对话中,创作实践和批评才能同步成长。
刘钢:多年前影像的概念还只是照片、图片,但在六七十年代开始,16毫米机器开始普及,影像才开始涵盖录像。现在我们谈论的影像包括多种数字媒体,在此基础上从艺术家的角度理解今天展出的作品:马良先拍广告,也拍照片,现在是木偶戏导演,处在不断跨界中,他的起点不是影像本身,而是多角度的,这也使他的作品与其他人不同。王宁德在开始是以摄影师的方式介入,后又转换为对光的研究,这是种当代艺术思维方式,也展现出他从摄影师往视觉艺术家的理解方式的转换。王国锋的拍摄受到图片时代挤压,是对现场感的感受。冯原从建筑视角做摄影,有一个综合的思维方式。还有苏文的作品对老底片进行扫描,甚至忽略了拍摄的过程,这是对图片价值的重新评估。
“再”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讨论美术馆与影像时代的冲突,当把展品按空间隔开展示时,个人本体的语境已经丧失了,造成影像被碎片化,这是展示影像时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怎样把作品的呈现方式还原到一个艺术家的语境中,和观众产生对话,这是被大众摄影不断普及所迫造成的结果。80年代后中国开放,图片应该增加,但题材却减少了,所有人蜻蜓点水地进入,但没有真正成系列的。艺术家不再以摄影师的身份出现,而成为策展人。这是对摄影师职能的消解,也是“再影像”中对摄影师身份的困惑。
谢慕:第一,关于“光的实验场”,展览呈现了对60、70、80年代不同年龄阶段代表性影像艺术家的再梳理,大部分作品也是这些艺术家近年来创作系列的延续。这些作品是否具有实验性,构成我们想象中的实验场,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第二,“再影像”。经过多年湖北美术馆“再”系列品牌展览已经深入人心。这次“再影像”,策展人杨老师认为“再”是超越和拓展。回溯2014年,策展人孙振华对“再雕塑”的理解和解释是对2012年雕塑展的回应,可见每位策展人对三官殿一号品牌展览的“再”字的理解和推动是和时代密切联系的,这也是策展人和美术馆结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点。
在美术馆中看影像作品,如果没有意思观众是不会花时间看的,这是一个传播效应问题,对美术馆和媒体来说,都是未来需要考虑的。
徐亮:从当代艺术的角度来讲,摄影始终具有当代艺术的属性,商业广告摄影和观念摄影、观念影像完全不是一回事。
就展览作品来说,第一,摄影作品不管是概念还是影像,从历史观照来观看当代是最有意义的,也需要和我们生活相关。而从历史的挖掘这个角度,中国的艺术家,包括我本人都需要去学习。第二,无论是传统观念摄影或是其他,作品所表达的主题和意义都是从人类生存文明发展和社会困境的问题出发的。摄影的语言、表现形式是外在的,有的人直观地做,有的人晦涩地做,有的人技巧地做,这都是每个人的技巧不同,也就有了天壤之别。
李裕君:我有三个关键词:光、数字时代、再影像。
“光”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不仅是作为影像,整个艺术各个形式都是离不开光的,包括每个人的生活也和光有关,今天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实验场去谈的光的概念。“数字时代”、影像从艺术角度来说完全没有进入一个概念当中,在近期才被当做一种艺术形式被关注。在数字时代,这恰恰是从技术层面给予了影像一个进步和延伸。“再影像”是对影像的一个重新认识,让我个人有种亲切感。
郑梓煜:我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我对这个展览策划的想法。
第一,分裂。大家都在讨论边界、定义的无效,它是一个现实,但是难道探求一个明晰的边界比感受具体的作品更重要吗?
第二,激进。这个展览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影像作品创作中“自由的困境”,其中包括创作的困境,观看的困境,批评的困境。创作的困境让艺术家有比较大的自由度,太自由了,没有边界了,对艺术家来说有时候并不是好事。而观看的困境,不仅是公众,而且专业人士和非常资深的批评家都提出“看不懂”的问题。这也成了批评的困境,离开绘画批评的框架,如何做影像批评?在中国语境下,从事新闻和纪实摄影的人觉得摄影有表现现实、表现苦难、去唤醒道德力量的天然职能,摄影推动社会的进步,如果将摄影前加上“艺术”二字是不对的。这也成为我们今天做展览时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我们不能用停滞的、过时的评判标准讨论一直在变化的艺术实践,而应该适应概念的混沌,将之当做一种常态的背景,再在这个背景下去讨论具体的作品。
每一件作品都有它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不需要有答案,艺术家也不必解答,而是通过这种媒介提出自己的问题和思考。这个展览中我们不应孤立地讨论某件作品,所有作品在一起会时会构成一个场域,形成一种张力,某种意义上也构成对中国近一二十年影像艺术实践的梳理。
冀少峰:三官殿一号艺术展走了五年,2011年叫“中转”,后来是“雕塑2012”,“再雕塑”,“再肖像”,到今年的“再影像”。这个过程离不开策展人、批评家、艺术家和媒体人的支持。今天这个展览的呈现,孙老师提出来影像和美术馆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不断的沟通的过程,这个沟通既有国际间的沟通,还有国内的沟通。影像对于美术馆的未来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而影像在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艺术是否介入影像艺术的观念肯定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对于一个美术馆来讲,美术馆的价值规范和价值趋向的确定,如果都看得懂了,美术馆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有一句话是:伟大的艺术永远不是迎合公众的,而是征服公众的。我们今天需要在焦虑的社会中静下来来看。
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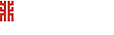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