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涅斯•瓦尔达女士与湖北艺术家面对面”交流会

“阿涅斯•瓦尔达女士与湖北艺术家面对面”交流会现场
交流会
整理:仇海波
地 点:湖北美术馆艺术交流中心
时 间:2012年4月16日下午
与会嘉宾(以发言顺序为序):
冀少峰 湖北美术馆艺术总监
阿涅斯•瓦尔达 法国著名新浪潮导演、艺术家
刘纹羊 艺术家
孙炜炜 艺术家
菲利普•皮盖 法国著名艺术家
龚 剑 艺术家
子 杰 艺术家
李建春 青年批评家
涂 清 出版人
傅中望 湖北美术馆馆长
冀少峰: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阿涅斯•瓦尔达女士与湖北艺术家面对面”交流对话会现在开始。非常高兴今天来了这么多艺术家,根据活动的议程,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这次活动的嘉宾主要有法国艺术家、导演——阿涅斯瓦尔达女士,坐在她旁边的是法国著名的评论家菲利普•皮盖先生,他是印象派大师莫奈的曾孙,还有克莱尔•塔布莱女士,法国驻武汉领事馆的文化专员,湖北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傅中望先生,湖北美术学院教授、著名艺术家魏光庆,湖北美术学院教授、著名艺术家袁晓肪,艺术家路昌步、李文、李郁,青年批评家、策展人李建春,青年艺术家龚剑、祝虹、詹蕤、陶陶、刘纹羊、王静伟、王晓新、王清丽、林欣、高虹、刘晓峰、子杰。还有这次展览画册的设计者麦巅,出版人涂清,以及湖北美术馆各个部门的工作团队。
瓦尔达女士不喜欢严肃的场面,她喜欢跟艺术家在一起进行非常轻松的交流,所以我们这次采用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下面我们就进行自由交流,大家看了她的作品之后,可以谈谈自己的感受或想法。
阿涅斯•瓦尔达:这次交流是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作品,还是你们自己先谈一下对这些作品的印象或感受?
冀少峰:我觉得还是先请瓦尔达女士先谈一下。
阿涅斯•瓦尔达:在展出《土豆乌托邦》作品的展厅中有一个很小的窗口,上面放映了关于土豆的影像,另外在一个很大的展厅中也放映着《土豆乌托邦》的影像。因为我对社会消费品的抛弃很感兴趣,所以我开始对土豆进行了一些研究。在法国的大市场或者大超市里,这些出售的土豆首先要进行外形的筛选,让它们符合体型的标准,不符合体型标准的土豆就会被扔掉。我关注那些被扔掉的土豆,而且发现了各种各样形态的土豆,有很多都特别肥大,有看上去奇形怪状的,也有心形的。我对这些心形的土豆特别感兴趣,对我来说心形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爱心和感情的象征,这种象征和最谦逊、最普通的植物蔬菜联系在一起。我开始把他们搜集起来,并且试图展现土豆不断老化的文化。我的镜头记录了它们渐渐老化的过程,另外,我选择了三联式的展示方式,这是一种早在15世纪诞生于北欧的一种展示方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种形式?我先在这三联的中间一联画上呼吸的土豆,并在后面配上呼吸的声音,然后在旁边两联的影像中展现这些老去的土豆开始迸发出新的生命的影像。在这些被我们抛弃的、老去的、腐败的、死亡的,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的小蔬菜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有新的生命慢慢孕育出来。为了能够跟现实联系起来,我又把一些真实的土豆铺在三联下面,这个形式完全是自然而然想到的,而不是特意去寻找的,完全是从我个人的体验中所找到的灵感。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评论或者感受。
刘纹羊:我是湖北美术学院的老师,在这里很高兴见到了阿涅斯•瓦尔达女士。我第一次碰到瓦尔达女士是在法国的里昂双年展上,她的作品当时对我触动很大。我的问题是,瓦尔达女士经常参加一些当代艺术展,但她本身是搞电影创作的,对她来说,电影跟当代艺术的关系是什么?
阿涅斯•瓦尔达:电影可能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具有标志性的运动,比如我们可以在大屏幕上看电影,或者使用一些电影特效,但不管它的形式是什么,都叫电影。电影界自始自终存在着一种具有研究倾向的作品,但不管在什么时代,这些比较前卫的电影始终是和现代艺术紧密相连的。一些画家也有拍摄电影的经历,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家拍摄了一部关于舞者的小电影。其实,电影这个形式不一定要强调一种故事,有时候我们拍摄一些短片,它可能只是一种影像的连贯或影像的运动,不一定在讲一个故事,而是一种感情的延续或连贯。电影本身的形式成为了它的主题,你们当中可能有很多艺术家都在从事录像艺术的创作,你们创作的这些作品也可能并不全部被大众所接受,或者流行于大众的消费体系中,但这些探索都是必要的存在。
孙炜炜:拍摄《土豆乌托邦》和当初拍摄《拾穗者》在思路方法和个人感受上有什么不同?
阿涅斯•瓦尔达:实际上《土豆乌托邦》是《拾穗者》的后续。当时拍《拾穗者》是应题创作的,当时主要为了记录在消费社会中贫困群体的生活状态,其实也是拍摄关于“消费”和“抛弃”,拍摄那些去捡拾我们抛弃的东西的人。虽然我拍的电影风格形式比较自由,但它毕竟就像社会学性的论文,而这个呼吸的土豆作品本身就可以传递出一些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信息,而且传递出了一种腐烂的情境,以及这些情境给我带来的感受。以电影所不能展现的另外一种方式来展现腐烂的土豆,这在动机和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
孙炜炜:创作影像和创作艺术作品,您在内心的体验上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阿涅斯•瓦尔达:我拍摄了很多年的电影,到现在一直都很感兴趣。我一直都有做装置艺术的愿望,但是我当时不太敢去创作,可能需要作出一种大的尝试和改变。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桥梁,当时鼓励我做这个事情的人叫汉斯奥•普利斯,他需要找一个非装置艺术圈子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才开始迈出装置艺术的第一步,并且选择了《土豆乌托邦》这个作品。在威尼斯双年展上我遇到了皮盖先生,当时在装置艺术界,我是一个外人,现在我想请皮盖先生来谈一下当时他们这些内行家对我的土豆作品的印象。
菲利普•皮盖:我第一次遇到瓦尔达是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就是在当时《土豆乌托邦》作品展出的地点。在我遇到她之前,我已经了解了很多关于瓦尔达的事情和她的作品。
我想强调一点,刚才你们主要是谈瓦尔达和现代艺术的关系,但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是瓦尔达本人对于艺术的理解不只是某一个特定的艺术,而是总的艺术观念的关注和见解,有可能是现代艺术,也有可能是传统艺术,甚至可能是非常古老的艺术。她的《土豆乌托邦》作品采用三联式,这是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形式,对我来说,《土豆乌托邦》这件作品最有意思的可能是某一个艺术时代或者艺术作品的变形,当我对土豆这个物质开始做出提问的时候,首先我想到的是土豆这个物体之前被什么样形式的艺术或者某一个有名的艺术家曾经使用过。当时首先进入到我脑海的就是梵高的《吃土豆的人》这幅作品,这个作品可能既不是很古典,也不是现代作品,但它立刻就让我对瓦尔达的《土豆乌托邦》作品有了比较感性和细致的认识。我不知道当时瓦尔达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梵高的作品,但是她的《土豆乌托邦》作品和梵高的《吃土豆的人》作品之间所呈现的关系让我确实感受到她的一种谦逊和艺术家的胸怀。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对梵高作品特意的致意,但是她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与梵高作品之间内在的一种联系和传承,这种艺术在不同形式中进行传承,包括文艺复兴时的形式,再到梵高的这幅画,再到瓦尔达作为电影导演在不同艺术形式中的流通和传承。对我来说,艺术始终都是现代的,可能我们会在整个艺术史中捡拾各种各样的片断,但无论怎么说,艺术总是有现实的意义,有现代的意义。
阿涅斯•瓦尔达:在我的冰箱上有块小的磁铁,上面是我搜集的从世界各地博物馆中购买的纪念品,冰箱的外面看上去像一个小博物馆,但是梵高《吃土豆的人》这张作品并不在我的冰箱上面。刚才菲利浦先生用了“谦逊”这个词,这种谦逊并不是表现在我对一些比较贫困,比较可怜的阶层的人的一种同情,而是对这些谦逊的人,谦逊的物体的一种感情的投入,并把他们作为艺术创作对象表现出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把这些被抛弃的物体表现出来。他们自己本身有自己的价值,有自己的美,有些艺术家创作的时候会故意把海报撕烂,或者拍一些比较斑驳的墙壁,这些艺术家在开始创作的时候起初可能并不是要把表面上很干净的东西作为他们创作的对象。你们作为艺术家应该很能理解在创作的时候肯定是会涉及混乱无序形式的表达。
龚 剑:我想回到刚才第一个论题,关于电影和当代艺术,以及现代艺术。这个话题涉及比较本质的问题,到底我们认为电影是什么,或者艺术是什么,这两个词后面有一个本质吗?实际上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电影有电影的本质,电影本身是什么,电影本身可以说是白日梦,是光,或者时间,或者是时间和空间的集合,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出艺术背后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艺术是什么。所以我认为这个话题非常复杂,但是我认为在瓦尔达的作品中,不管是她的电影或者是装置里面都有几个很重要的地方,其中一个就是关于时间,时间可能是瓦尔达比较感兴趣的东西。
阿涅斯•瓦尔达:昨天晚上的放映出了一点小问题,当时我正好解释了对于时间观念的理解。
龚 剑:昨天我还看到子杰写的电影感受。其实我早在之前就看过你的几部电影,有一个是《5时至7时的克莱齐奥》,我感觉您实际上是想讨论关于时间的话题,但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电影在讨论时间的话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空间。这个电影的主体作为一个对象,以不同的方式在城市空间当中不断变换它的方式,比如有的士、自驾车,还有中间一个人在公园里漫步,我认为它主要是反映个体在城市空间中以不同的速度在另外一个空间里游荡的过程,我觉得“游荡”这个词是对这个电影一个很好的注脚。
昨天我在现场听到了瓦尔达向我们介绍这个电影,她强调了时间,后来我想到了《柯布西耶的露台》和《土豆乌托邦》,我觉得这恰好体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关系。首先在影像中可以看到土豆在发芽,在腐烂,我们在五分钟之内就可以看到土豆从一个好的土豆变成一个烂土豆,而且在屏幕的下面有很多真实的土豆,如果这个展览持续一个月的时间,我最后再来可能会看到真实的土豆在变烂。
阿涅斯•瓦尔达:现在在法国南部一些城市同时正在进行《乌托邦之薯》的展出,一直持续到下个星期天,因为这个在法国南部的展览是去年12月开始的,下面那些真实的土豆已经开始发出小芽了,已经不再具有心的形状了。
龚 剑:后来又看到《柯布西耶的阳台》,我觉得那个阳台作为一个空间,可以承载时间,它是一个时间的容器。实际上从这两个影像中,我看到瓦尔达是想讨论在一个静止影像的前一秒或者后一秒发生了什么。我更感兴趣的是,在同一个空间是50年之前和50年之后这样一个巨大的时间,但空间还是50年之前的空间,演员已经是另外的演员。我想起中国有一个艺术家叫海波,他拿了30年前的一张照片,找到同样的这一批人,然后在30年之后以同样的构图拍摄同一张照片。回到刚才最初的话题——艺术和电影,因为我看过您的一部电影是关于一个女演员,87年的一部电影,其中有一个场景是一男一女,好像是一个书店里,他们在谈论和看很多画册,是《千面珍宝金》,有很多书,有沃霍尔,有霍克尼,马蒂斯,是一个拼接的。我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导演,瓦尔达对绘画和对艺术话题非常有兴趣而且非常有研究的。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本质化,认为艺术有一个本质,这是非常危险的。我知道瓦尔达在做电影之前也不是一个学过电影的,我不认为会有一部分人认为她是一个导演,所以她来做艺术,我认为这之间没有什么界限。
阿涅斯•瓦尔达:我很感谢这位先生对我作品的关注,有很多元素我都会很感兴趣,尤其是时间空间的概念。对我来说,每一张照片可能都是一部未完成的电影,一张照片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在一个运动中的时间,捕捉到一个瞬间,这一瞬间分开了之前和之后的界限。在拍电影的时候我的摄影机会有一个框,我非常感兴趣的就是这种画外的东西,在摄影机框之外存在的东西,不管在左边、右边还是在其它什么地方,而在《露台》这个作品中我只关注时间这个概念,不管是1956年到2006年这样一个时间的跨度,还是在这两个作品之间的时间跨度,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它存在于现实。它并不是真实的,就是因为它是重塑的,我重塑了里面的人,后来请了人,重新穿了服装,重新摆了姿势,并不是当时真实的人。所以当我重塑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完全虚构和虚假的现象,比如说里面正在照相的人并不是真的这个小孩的妈妈,有可能是他的邻居或者是亲戚,可能另外一家人根本就不认识那一对,可能就是一种想象的重塑,是一种可能完全自由的组合。但是正好其中妈妈的角色又跟50年前拍的照片很相象,我们不只是拍摄到时间的前后,而且拍摄出了空间的前后感。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荣幸,一种训练,所以在“克莱齐奥”电影中,我所想尝试的就是对时间进行发掘,进行研究,研究现实时间和电影时间。如何把钟表上体现的机械时间,永不停歇的时间,和主观的我们自己所感受的时间相联系起来,因为主观的感受时间可能有很强的弹性。对我来说,电影是谈论这个话题最好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在土豆作品中,老的土豆和新的土豆时间上的演化,可能在我们自己看作品的时候体会到人与人之间不同时间的进程演化。这种土豆其实是很老的,里面发出新芽,新的生命的诞生可能是基于旧的东西毁灭的基础之上。
让洛克多曾经说过,电影可能死在工作中,不管是什么样的电影创造,它总是有一种想要制止时间流逝的情绪,在这个时间中一切看上去都是转瞬即逝的。在创作“猫的坟墓”作品的时候,我们当时的状态比较放松,思念的是被埋在花园中的宠物,同样里面还采用了一个小的仪式,里面又融入了一些元素,当我们慢慢开始远离墓的时候,感觉这个墓慢慢变小,一切的存在,不管是死去的猫,还是人,或是土豆,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在这个巨大的世界中,我们从越来越远的距离去观看一个小小的土豆,就显得非常渺小了。我这是不想贩卖廉价的哲学,但是我想表达的是死亡和毁灭这样的主题,它可能也会传达出比较轻松的信息,以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呈现出来。
子 杰:我想谈一下《5时至7时的克莱奥》关于时间方面的问题。关于剪辑,对每一个镜头的加头去尾是存在的,电影里面的时间和现实中的时间形成了两个世界。
龚 剑:电影镜头里面土豆两个小时就腐烂了,但是现实中可能需要一个月。
阿涅斯•瓦尔达:在剪辑的时候,镜头多多少少会有遗漏,在镜头剪接上可能会有时间的断裂和空隙。
子 杰:她掐得非常好,克莱奥家里有12级楼梯,我说的是电影里面的时间要比真实的时间要长,是因为剪辑而造成的,如果用长镜头来全程不间断的跟拍,这实际上只能有一种时间,但剪辑让电影和现实时间分开了,变成了两种时间。
阿涅斯•瓦尔达:当我们在放映电影的时候,除非是长镜头,或者是一个胶片不切换的一直放映,对我来说时间的延续,我并不是特别关注。
子 杰:我觉得长镜头的时间和剪辑的时间会造成很多不一样。
阿涅斯•瓦尔达:长镜头的意义就是镜头一直跟着拍摄物体,中间不间断,在希区柯克的《夺命索》中,就是九卷胶片连续放,不间断的,其实并不是移镜的,只是做了移镜的印象。索科洛夫的俄罗斯方舟也是从头到尾移镜下来的,在克莱奥作品中可能要展现两个方面,一是对时间的延续,二是要从不同的视角来展示时间。比如《5时至7时的克莱齐奥》,我展示的是安吉尔和模特朋友在一起的段落,因为那个女的是一个很现实的女人,所以当时用的镜头是距离比较远的,比较开放式的镜头,比如说在5点20到5点30时间段中,我想展示克莱奥非常柔和非常平静的状态。
其实在研究时间延续性的主题上,我也希望通过不同方式展现时间的进程,我想在这90分钟时间里来展示克莱奥这个人物的演化和变化,比如说克莱奥在电影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娇宠,非常自恋的,被万千宠爱,自视甚高的漂亮女人,当她听说自己有可能生病,有可能会收到死亡威胁消息的时候,她开始感受到恐惧,而这种恐惧让她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然后她把自己的衣服假发都摘掉,她开始走到街上关注别人,她的视线开始放到其他人的身上,在展示过程当中,的确有剪辑的痕迹在里面,所以并不是严格线性延续的时间。
龚 剑:我还有两个问题,既然是导演有意识的要讨论真实的时间问题,那么在克莱奥下楼的时候有三个不断闪回的面孔特写。这个闪回的特别和时间线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阿涅斯•瓦尔达:其他人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子 杰:我也想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片里面应该存在三个时间,一是电影里面的时间,二是现实的时间,三是作者和观众合谋的时间。最开始克莱奥下楼梯三个重复的脸部特写就是属于作者和观众合谋的时间,是作者想强调或者想对其进行评价,从而让观众可以看到更多。
阿涅斯•瓦尔达:有没有感受到当你得知一个噩耗的时候有一种迎头一棒的感觉,所以特别强调从楼上下来的镜头,是真实时间的展示,其实这三个镜头并不是同一步的三个重复的镜头,而是不同的三步,是下了三次楼,所以要表示在这瞬间接到噩耗时对整个人的一种冲击,里面配的音乐正好配在剪辑上。可能在下楼梯的过程是时间的,而是通过剪辑给观众留下一个特别强烈的印象。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关注是作为一个创作者,作为一个艺术家可能会存在个人的一些私人动机,而当时我不想传递给观众的是这是一种普通的情感,感觉好象是连续三次的强烈冲击,其实在时间上是连续的,这是我们电影工作者的工作,我们既要使用一些技巧,一些专门的特殊材料,但有时候要有一种低调的态度。
龚 剑: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在片头看到占卜者玩塔罗牌,他说你的生命中会出现几个什么样的人,有寡妇,有一个很会说话,很会讨她欢心的男孩,但是最后看完电影,我就感到这些人在影片中全部出现了。作为一个影迷我很想听到导演确切的告诉我哪一个是哪一个?
阿涅斯•瓦尔达:这是我1961年拍的,这么老的电影如今还能激起这么多人的兴趣我很高兴,我希望你们也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在50年以后能影响到那个时候的年轻人。
我当时是真的去问了一个玩塔罗牌的职业占卜者,我当时找到他的时候,跟他谈论了关于电影的故事情节的问题,比如说会有一个守护者,在电影中可能是比较年长的请愿人,还有她的那个朋友,那个助手,塔罗牌中以一个女性保护者的形象出现,当死神那一张牌出现的时候克莱奥会感觉非常恐惧,当时在牌上看到的并不真的是一张死神的牌,那个人的身上还是有肌肤,有血肉,它只是意味着一种转变,并不意味着死亡。占卜者肯定会这样说,后来又一个镜头她跟丈夫说看到的是死亡,后来会说你碰到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就是邀请阿尔及利亚士兵,作为一个占卜人给你们展示这些牌,告诉你们每个牌意味着什么样的人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其实是为了给你的生命带来一种希望。
而我作为电影创作者,当时我拍克莱奥是黑白电影,但是我把占卜这一部分拍成彩色的。因为对我来说,玩牌的这一幕,牌所展示的故事叙事可能是虚构的东西,克莱奥在进行占卜完之后,她意识到这个牌里所讲述的事情会成为她现实中的遭遇,所以激发出了她的一种恐惧心理,因为当时彩色电影颜色非常鲜艳,而黑白片是用非常普通的胶片拍摄的,而如今黑白的影像反而显得更加珍贵更加稀有,这就是50年的差异,有很多人都曾经研究过这个电影。
李建春:我想谈一下对这个作品的感受,特别是《乌托邦之薯》和《柯布西耶的露台》。我感觉你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乐观主义者,你总是在思考死亡,但是几乎你的所有作品都战胜了死亡。我对《乌托邦之薯》的感受跟时间和死亡的主题非常明显,但是我对它的感受不是腐烂,而是发芽,是生命的一种转换。这些新鲜的土豆随着时间流逝发芽皱缩的过程特别感人,我想这是一种有爱和富有生命的形象。
阿涅斯•瓦尔达:我当然要特别强调一下,你们在我作品里面还应该要注意,正因为我的年纪,你们更应该能感受我的艺术中所蕴含的能量。一个年长女性的强大的气场。
李建春:皱缩、发芽,具有新生命的形象,这让我想到艺术家本人。刚才您说电影死在坟墓中,这句话是一个艺术家最崇高的表白。
阿涅斯•瓦尔达:电影是记录死亡的过程。
李建春:我把土豆视为艺术家的自画像,三联式的形式常见于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宗教性的绘画,这种形式特别擅长表现一种崇敬感,但艺术家用这种很严肃的形式来表现土豆。我认为瓦尔达用一种神圣的情感去看待土豆的皱缩和发芽。
刚才皮盖先生提到梵高的《吃土豆的人》,在梵高的作品中这些土豆是一种平凡朴素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瓦尔达女士作品中,土豆就是生命本身。我再想谈一下对《柯布西耶的露台》的感受,我想这个作品涉及怎样对待一张照片,艺术家作为一个摄影家拒绝用消费主义的态度对待照片,英国有位批评家叫约翰•伯格,他认为我们对待照片的方式应该把照片还原到一定的语境中。在我们现在这个影像泛滥的时代里,照片容易成为一些苍白的幽灵,因为照片在我们眼前被剥夺了它的上下文语境,剥夺了记忆,艺术家试图还原照片中早已遗失的记忆,然后采用一种虚构的想象的方式。
瓦尔达的作品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女性的特质,女性的感受和视角,这种女性特点对于您而言是非常自然体现出来的,而不是用一种女性主义的观念。您的《5时至7时的露台》,虽然是一个50年前的作品,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的主题都是主人翁遇到死亡,但是最后都轻轻地越过了。我对您的《茨古古的坟墓》,还有大海的照片,这些作品都非常喜欢,还有那些装置,非常富有想象力,我非常喜欢,非常优秀。
阿涅斯•瓦尔达:这是我们对彩色装置艺术的一种展示,我们在现在全中国也没有看到这样的装置艺术,大家总觉得土地树木很漂亮,对我来说塑料一样漂亮,因为塑料的五颜六色的彩色让我感受到维他命的药丸。
李建春:非常荣幸能够看到您本人和您的作品。
阿涅斯•瓦尔达:在《土豆乌托邦》作品中,三联式最开始是宗教画的形式,但放在中间的土豆并不是神圣的宗教性的东西,而是在呼吸的心形的土豆,非常平凡,非常具有生命性的象征。我要表达的不是一种战胜死亡,而是每次我们都能在艺术中找到新生的感觉。我跟其他人一样也不可能战胜死亡,但是在艺术中我能找到新的生命的寄托,今天早上有人发邮件跟我说您拍摄的作品虽然非常沉重,但是您本人看上去是非常乐观的老太太。
在波塔斯基的作品中也总是出现死亡主题,里面出现了死亡和剥夺人性的主题,他本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开朗,非常有趣的人。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创作的特色并不一定是本人性格的一种体现,有时候我们内心所想要创作的东西可能并不跟日常生活有紧密联系,内心创造的需求其实独立于现实,独立于日常生活。创作方式并不是哪天早上突然起来,把自己面前放一张白纸,就开始说我现在是一个艺术家,我要开始创造了。我们家有很大的浴缸,当我放一大缸热水,我泡在热水里面的时候会有很多主意,当我走出浴缸的时候可能把点子抛在脑后了,我又开始自己日常的工作,可能四天以后我又会突然想起来当时在浴缸中的点子,我那时候就想把这个点子实现出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准确的去控制它、衡量它。
涂 清:首先,我很喜欢瓦尔达,我认为这次在武汉看到这些展览,很多人没有提前看电影就直接看了,也许有一点遗憾,我认为阅读相关的评论和看电影,看展览,和读她写过的一点点文字,这些要结合起来,这非常重要。
阿涅斯•瓦尔达:当然我作为艺术家的梦想就希望是你们尽可能的了解我的作品,但是我们创造出的作品并不是每一个都会有很全面的注释。在座的各位已经在之前了解了我的作品,我觉得这样很好,但是我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这样。我曾经去过巴西北部的一个小城,当时那里的观众都会谈论关于我的电影中的一些特质和细节,观众的反映对创作者来说是最好的褒奖,在座的只是千千万万中国人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菲利普•皮盖:40年前我曾经了解到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主要创造的是身体、身份和变异的主题。我现在想到是一个他曾经做的一个录像作品,他把自己呈现在镜头前面,这个艺术家在录像作品中穿着浴袍在水里面,我们只能看到刚刚浮出水面的脸部特写,他脸上覆盖着一层橡皮泥,是三种不同的颜色,这个作品的主题是一种面具,而面具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死亡,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面具》。在很短时间的录像过程中,记录着他慢慢从自己脸上抹掉三层橡皮泥的过程,让自己的真实面孔呈现出来,所以在这个作品中呈现出一种死亡的影像和生命影像的辩证。他有整个头露出水面的形象,本身流动的水也是一种生命的象征,固定镜头拍摄,持续时间不是很长,持续拍摄的是他慢慢用手把脸上的橡皮泥抹掉的过程,通过数码影像记录的是慢慢把脸上塑胶覆盖的膜抹掉,产生的是一种让观众和作品产生距离的效果。
我现在还想再补充一点点我对瓦尔达作品的观点,尤其是对死亡的关系。在西方,死亡这个主题在很长时间里面是一个禁忌的话题,除了中世纪以外,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个很有名的中世纪历史学家有一个交谈,而这个历史学家本身对很多现代艺术家的作品创作非常感兴趣,正是因为这些现代艺术家他们创作关于死亡的主题,而没有任何禁忌,因为死亡本身就是生命中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不应该对这个主题有所顾忌,我们对待死亡这件事情就应该以对待生命一样的态度,这种生命到死亡的轨迹应该是我们所要理解和重视的。不管是电影作品“克莱奥”,还是“土豆”,还是“露台”的作品中,在瓦尔达作品中都能体现出艺术的张力,行为所体现出的张力,这就是我对瓦尔达所最看重和敬仰的。
阿涅斯•瓦尔达:我还想补充一点关于幽默的看法,并不是取笑,而是要让你们在作品面前能够露出微笑,因为很多情景可能会隐含着一些幽默,我们自己本身可能会有幽默的情绪。当我说我是一个年长的导演,和一个年轻的艺术家,这样的遣词造句的方式可能会很有趣,但是是真实的。有一个叫阿尔弗来德雅米的诗人曾经说过,别人问他死前的最后意愿是什么,他要了一根牙签,这是非常经典的幽默。
龚 剑:刚才你们在谈论死亡,我同意皮盖先生的看法,但是我认为土豆作品中最重要的不是死亡。关于死亡的态度我非常喜欢苏格拉底的一句话:“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路最好,只有神知道”。土豆作品中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它去死,然后变成一个新的东西,而是直接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比如说它发芽,它不是死,也不是活,用德鲁滋的观点叫“生存”(becoming),我认为它这样去生存不是为了死,或者是为了生,它只是为了拒绝,和一种遗弃。它本身自己是被遗弃的,土豆是无法进入消费系统的,但是它发出了芽,是一种自我的遗弃,因为我们知道发芽的土豆是不能够吃的。就好像她的另外一部电影《天涯沦落女》,她本身是一个社会边缘人,她也不断拒绝了社会上的其他边缘人,将自我遗弃了。我觉得土豆和天涯沦落女的共同点就是孤独和遗弃,他们在自我肯定的同时其实是拒绝了其他所有人,拒绝整个社会体系和其他的人。就好像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那个人变成了虫子,他是为了和所有人隔绝开,他要逃离所有人,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死亡,比其他的东西更有力量,这是一种自我肯定,一种孤独的力量,这个是最重要的。
阿涅斯•瓦尔达:在《天涯沦落女》电影中,女主角的确是这种情景,但是对于土豆来说,土豆本身没有这个意愿,可能不是你所理解的,土豆不具备自主权,没有控制权。
龚 剑:我觉得这是唯物主义的说法,我觉得土豆也有自己的想法,这可能是命运决定。
阿涅斯•瓦尔达: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作品的关注,谢谢!应该由我来感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出席,谢谢你们对我的关注。湖北美术馆的馆长组织了这次活动,让我非常高兴。
刚才有一位老先生,在1957年我来武汉拍照片的时候,他曾经带着我去东湖,在这里能够碰到55年前我在武汉的时候曾经帮助我拍摄照片的人,我觉得非常感动。他是怎么想到的?怎么记起这是我的?对我来说,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让我感觉到一种时间的关联。
我要再次向两位馆长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组织这次会议,我也非常遗憾不能跟每一个艺术家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的作品,我祝愿他们能够有更加强的艺术创造力和灵感,还有一种可能会跟年轻一代并不是很相符的强烈的热情,一种对事物的执迷,还有感谢跟我一起来参加这次会议的菲利普•皮盖,著名的艺评家、年轻的法国艺术家克莱尔塔布莱女士,她来中国做三个月的交流工作,她从这次对中国的访问以及跟中国观众的交流会中学习到很多。谢谢大家!
傅中望:非常感谢瓦尔达女士,也感谢菲利普•皮盖先生。这次的展览非常成功,也引起了武汉各个媒体的高度关注。我今天看了很多报纸,其中有很多的版面都在宣传这个展览,我看到湖北的观众对这次展览也抱有极大的兴趣。
瓦尔达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她的作品能来到湖北,重返武汉,这是我们的荣幸!这些作品唤醒了我们对故去年代的记忆,特别是瓦尔达早期拍的照片,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影像,还是装置作品,都充满了这位艺术家的智慧和创造力。
在艺术各个门类中,装置和影像作品目前在中国还处在实验阶段。对于很多普通观众来说,这还是一种比较新的艺术形式和语言。这次展览无疑为湖北的观众,为湖北的艺术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让我们湖北的观众在艺术的领域认识一种新的艺术表达方式。
今天在座的艺术家们都是湖北非常优秀的,他们是在影像装置领域有着实验和探索精神的艺术家,也创作了很多很好的作品。他们有机会在这样一个平台当中能和瓦尔达女士在一起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瓦尔达其实是很自然而然的用不同的方式把她的内心情感或态度表达出来,没有什么很刻意的东西,她很自然地的运用这些不同语言来表达,显得很自然。今天的研讨会非常成功,我要再一次感谢阿涅斯•瓦尔达女士,谢谢您!
冀少峰:今天的研讨会是一个真正的交流会,大家交流得非常轻松自如,同时也体现了湖北青年一代对当代艺术的关注。湖北美术学院动画学院专门放假了一下午,很多青年教师来到了湖北美术馆,感谢动画学院的支持!同时,感谢法国驻武汉领事馆文化专员,感谢湖北美术馆的工作团队,感谢开关文化,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
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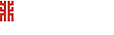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