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代:建构中国文化性格的现代文明秩序
冀少峰
中国目前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正遭遇的“成长之痛”,既是新旧冲突之痛,亦是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冲突。这种结构变局体现在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型,尝试从前现代、现代化的道路中走出,去接受当代的文明,从农业国家向新型工业国家的转型,从乡土社会向城镇化的转型,社会转型之痛必然带来文化转型之痛。
一方面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始终处于一种对立状态,五四运动以来,这种危机并没有根本消除,有学者称之为“后五四时期”文化危机。另一个就是“后文革时代”的意识形态危机。那是一种革命式、空想式、理想式文化贫瘠的危机。第三个危机则是1978年结束“后文革时代”危机后的一种后现代的心理危机,即当代社会所普遍弥漫着的焦虑意识。
由此不难发现,当下的中国已和传统意义上的中国、1949年以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30年的中国都是不同的,中国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全球化格局中承接传统与现代,如何沟通中国与世界。这其实也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明所共同面临的现代性困境,而现代性、现代化则又构成了百年中国社会转型的两个不同主调,而现代性转向其目标则是构建现代文明秩序,意即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发展模式和路径的重新认识、定位。
如果回到具体问题其实是一个再中国化的问题,即是对中国价值、中国模式、中国崛起、中国主体性的再认识,同时探讨传统文化如何适应并转化出现代价值,进而穿越传统为现代化设置多种屏障逐渐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过渡。终极目的是构建现代文明秩序,即价值系统、制度体系受经济、社会、政治、国际环境和文明形态转型。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走出一条多元现代性之路来,因而“再现代”既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又在一个永无止境的实验中……
一、两个标志性事件
米歇尔·艾伦·吉莱斯皮在《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一书序言中这样写道:“我们处在一个视觉时代。在过去20年间,有两幅图像大大影响了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理解:一是柏林墙的倒塌,二是世贸中心的倒塌。这两座建筑不仅仅是人工物,而且是深植于民众心中的象征。随着世贸中心的倒塌,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看待全球化,不再把它视为通往现代性的单行道,而是认为有大道、小巷和山间小路交错纵横。结果,我们不再期待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而是瞥见了侧面那些阴暗角落。”此叙述使我们清晰地洞悉到在这些事件背后,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事件,而且是标志性的事件。它标志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及深层次社会结构,经济秩序、文化身份认同、生存观念及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前一个事件则直接宣告了冷战时代的结束,世界由美苏两极走向了美国的单极化。而“9.11”事件,又迫使人类不得不反思,特别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因为“现代性的许多拥护者对此都感到难以置信。一个人有可能在道德上对现代性的好处没有得到更加公平或广泛的分配而义愤填膺,或者惊愕于现代工业社会对环境的影响,甚至沮丧于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摧残和蹂躏,这些都很容易理解,但怎么可能有人去反对现代性所提供的那些明显的好处,反对平等、自由、繁荣、宽容、多元化、代议制政体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呢?”这种源于人们心灵深处的诘问及对现代性的挑战,也迫使我们不得不返回现代问题的讨论。那么,关于现代性,通常的看法是“现代性是一个世俗的王国,在其中,人取代神成为万物的中心,并试图运用一种新的科学和与之相伴的技术来掌控和拥有自然。现代世界被认为是一个个体主义的王国,表象和主体性的王国,探索与发现的王国,自由、权利、平等、宽容、自由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王国。”现代性更应被理解成一种努力,试图为神、人和自然的本性和关系问题找到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神学回答。而大陆学者汪晖对这个巨变的社会亦有这样的分析:“就思想的变迁而言,大约到1990年代的中期,中国知识分子才从前一个震荡中复苏,将目光从对过去的沉思转向对我们置身的这个陌生时代的思考,这是一个诞生于1989年的大震荡之中的早产的婴儿,却必须面对空前的剧烈的社会重组。”汪晖的论述和吉莱斯皮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即“‘90年代’却是以革命世纪的终结为前提展开的新的戏剧、经济、政治、文化,以至军事的含义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若不加以重新界定,甚至政党、国家、群众等耳熟能详的范畴就不可能用于对这个时代的分析。”所以汪晖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冷战的终结与革命的终结相互重叠意味着这个时代既不是19世纪的跨越性延伸,也不可能简单搬用20世纪的政治模式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二、重返中国的现代化
百余年来的中国社会转型不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领域都在进行着“前现代型”向“现代型”的转变,但无论社会转型的怎么样,意欲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努力和意图始终未变。其间亦通过不同的社会变革来实现之。这其间既有“崇尚西学”的洋务运动,亦有运用改良的“戊戌维新”,更有直接推翻2000年帝制的辛亥革命。而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及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难发现,中国社会一步步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向。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文化要面临一系列的危机。近期,对甲午战争的反思,也从一个方面折射出我们的文化与心理危机。正是甲午战争,击碎了中国迈向一个新型现代国家的梦想。而来自于文化上的危机,一方面是五四以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尖锐对立,新近兴起的“国学热”无疑又为失去了近一个世纪的儒学重新找回其应有的位置。第二个危机则是“后文革时代”意识形态危机。如果说“文革”在思想文化领域存在持续“反传统”的立场,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却把自己完全“封建化”、“宗教化”、“传统化”。“文革”结束之后,社会秩序走向了重建,特别是1978年之后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使社会危机迎刃而解。但信仰和信念的缺失情绪开始在社会上蔓延。诗人北岛曾说:“烤焦的鱼仍然做着大海的梦。”但反观我们的生存现实和生存处境,虽然人们并没有被“燃烧的激情”烤焦,但梦回大海的梦想却再也难觅了。第三个危机是再现代的心理和心态危机。飞速发展的时代和巨变的社会使中国在迈向强国之路上,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挑战。虽然信仰的缺失,文化的俗化和商业化,越来越导致对资本神庙的膜拜。社会普遍弥漫着的是一种焦虑的生存情态。我们又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国进民退”现象,社会贫富两级分化日趋严重,社会阶层的固化,城乡之间的差距加大,及生态的破坏,环境的被污染,也都导致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建构现代文明秩序的紧迫性。诚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今日全球多元格局下,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绝不止是军事力量,甚至不止是经济力量,毋宁更是知识力、文化力,特别是它拥抱一套现代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权、公义、多元、王道、环保),说到底,它必须有一个现代的文明范式。”
三、转型社会与社会转型
为什么要把转型社会和社会转型拿出来进行专门讨论,也缘于转型社会必然导致社会的转型,必然导致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而转型社会既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是中国社会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这里面也牵涉到我们自身社会的两次转向,比如1905年的“废科举,设学校”,这导致中国学术思想和中国文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民主共和观念萌发出来,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都较以前发生了彻底改变。社会转型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政治的转型。那么转型所带来的变化又突出表现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由后君主王朝到民主国家的转型,意即政治的现代化。还有就是由经学时代向科学时代的转型,意即文化性的转型。其实构成社会转型关键词的就是从传统向现代的大转型。而改革开放所开启的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局面,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亦是我们在构建现代文明秩序的进程中所不能忽略的一个转型元素。
四、再现代:建构中国文化性格的现代文明秩序
“现代和现代性是自培根和笛卡尔时代以来思想所持有的自我理解的一部分”。现代化的问题是传统到现代的转变问题,而现代性于中国就是社会制度的不断改革,在社会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它迫使我们提出新的思想方式和存在方式,寻找一种新的答案,进而重塑我们居住的世界。这也揭示出了再现代的核心文旨,就是理解中国问题,还需从中国实际出发,反思我们的处境,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
秦晓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一文中这样表述:“中国的社会转型,即从一个前现代(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性社会。这一转型自晚清始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历程……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语)。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对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呼唤。”而博源基金会、《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编辑小组在“编者的话”中亦有这样的论述:“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跨世纪的,至今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由此不难发现,当中国前现代社会的传统文明秩序解体之时,而一个适应现代社会的现代文明秩序又远远没能建立起来。一方面,西方世界的现代性已然在反思自身中不断修正前行,而中国再现代历程,一方面在汲取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从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亦获得某种启示。第三,透过再现代视角,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一个具有中国文化性格的现代文明秩序,将是一代甚至是几代人要完成的努力目标。
由此,亦可看到,中国的当代艺术历经30年的发展历程,是和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联。它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段,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面对都市文化的生存、观念形态的更新、大众文化的兴起、图像时代的来临、全球化的冲击,使得艺术不能孤立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文化思潮的更替之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你很难再用一两句话对当代艺术的发展态势给予一个概括性定论,它至少给我们这样的提示:一方面,新世纪的当代艺术发展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格局中,另一方面,也由于当代艺术的动态性、即时性,也导致了它的语义的多义性、叙事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多元性。
近十几年的当代艺术,一方面又呈现出一种多元现代性的并置状态,另一方面,它还必须面对问题意识,立场意识,价值认同和批判精神。而当代艺术正是由于其在启蒙过程中的先锋性,在完成现代性的过程中它的立场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紧迫性,在使现代性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完成它的超越、反思与创新。可以说,近十几年,也是当代艺术超越、反思和不断创新的年代。
这一阶段的当代艺术又呈现出的是另类的繁荣与昌盛。美术馆时代的概念流行,各类艺术区、民营艺术机构的层出不穷,双年展或三年展的重复与雷同,跨国商业画廊的深度介入,境外美术机构的购藏,国际策展人的推波助澜,国际展示与交流的频繁,画册及各类出版物的无限流通,特别是市场与拍卖所共谋的种种骗局,虚假的拍卖纪录,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艺术界蒙上了一层虚假繁荣的面纱。
而当代艺术的多样性显然也不是由单一的价值所决定,新的社会形态所表达出的新的视觉方式和多样性相并存,无疑丰富并发展了多样性的艺术态势,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透过参加“再现代:第三届美术文献展”艺术家的视觉表达及精神的诉求,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当下社会的变化及我们共同面临的生存处境和生存困境,他们以自我在视觉文化上的创新,深刻地反思全球文化格局的文化冲突与融合问题,及急速变化的社会现实所带来的焦虑体验,这其实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差异化的视觉表达方式带给人们的其实是社会变化所带来的速度感、紧张感和戏剧性,而恰恰是这种速度、紧张和戏剧性,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就把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文化身份、生活习惯、价值认同来了一个彻底的颠覆,它体现的不仅仅是艺术家们对现代性的差异化理解,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社会实践,其实是一种精神再生产过程,这一精神再生产过程带给人们的则是一种对欲望和诱惑不可逃避的现实。
而当下中国社会仍处于现代性的讨论中,特别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混搭,恰恰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而当代社会又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再现代相互交织缠绕的并存状态,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秩序、社会文化命题关注点都在发生着激烈变化。这导致艺术的关注点已远远超越了风格样式、语言材料这些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但生态、环境、文化身份认同、女权、生存与权力、本土与全球、民族与地域仍是艺术界的话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都导致艺术家们在对当下社会现实和文化价值进行着激情思考和洞察性表达,但参加“再现代:第三届美术文献展”艺术家作品背后所彰显出的问题意识、立场意识、价值认同和批判精神才是当代艺术真正的力量所在。
2014年8月20日下午3:20
于东湖三官殿
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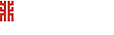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