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漆艺的时代碰撞
冯健亲
近三十年来,关于“漆的艺术”的讨论似乎从来没有停息过:一方面,漆画独立画种地位的确立,使得漆画名正言顺的从传统手工艺转化为纯艺术,从而获得了在艺术创作领域驰骋的广阔空间;另一方面,在现代艺术思潮盛行于中国的大背景下,形式语言在艺术创作中的本体地位得到确立,从而使得中国漆艺在突破和发扬传统方面获得了新的动力,并以其独特魅力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现代艺术领域的新成员。事实上,无论古代还是今时,漆艺从来就不单单是一个材料工艺的问题,有时它甚至会超越艺术本体,反射出文化与时代碰撞的火花。
一
追源溯流,河姆渡文化出土的髹漆木碗作为最早的实物证据,将中国漆文化的历史定格在了七千年的时间维度上。最初,先民们使用漆主要还是看重它的实用功能——漆树汁液涂抹于木器表面并干固后,能够使得器物更加结实耐用;而木碗上的朱漆,同时显现了先民们的审美欲望。之后渐渐的,人们将色漆用于纹样的描绘,在保护器物的同时起到美化的效果,至此“漆艺”一说才算真正揭开了序幕:像战国、秦汉时期的漆器仍以杯、盒、瑟、棺等实用器具为主,器物造型和漆的工艺技法相辅相成;而南北朝之后出现的漆屏风等平面形式,则更加注重漆工艺在画面表现上的运用——这种趋势到了明清时期更是走向极端,发展出像百宝镶嵌这样极致奢华繁复的陈设品。可以说,长久以来中国人使用漆来制作器具、装饰环境的经历,以及由此积累下来的在材料、工艺乃至审美等方面的经验、共识,共同构建了中国漆文化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
就漆材料本身而言,它至今仍在日常生活当中具有极其广泛的运用,但是上升到文化层面的漆艺,却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审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了复杂的面貌。以战国、秦汉时期来说,漆器由于具有物面光亮、色彩富丽,且胎型不受限制、轻巧方便等特点,逐渐成为了王公贵族日常使用的首选,大有取代青铜器之势。然而正是由于被纳入到了上层阶级的视野中,他们为满足生活的享受,不惜花费大量人工及金银珠宝以提升漆器的华贵程度,以致其逐渐脱离实用而更多的走向审美。但是这一转型似乎并没有遇到一个好的契机:由于成本更低、制作更为便利的陶瓷器的迅速发展,漆器作为日常用具的功能被彻底取代;同时,由于绢、纸的发明以及卷轴画的出现,使得漆艺走纯绘画道路的可能,一下子也变得渺茫起来。
我们知道,绢帛以及适用于绢帛的矿物颜料的出现,使得中国绘画艺术确立了以卷轴画为主体的基本结构,之后的纸、墨则是这一形式在材料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应当说,卷轴画地位的确立对于中国绘画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相比于漆器的制作,卷轴画创作在材料上的约束要小得多,过程也更为轻松便捷,自然也就更利于艺术家主体思想的自由表达。西方先民一直与大漆无缘,到了中世纪后期,有画家发明了油性颜料,画面材料则由木板过渡到将帆布绷在木框上,创造了属于西方文明的新画种——油画。中国传统漆艺在与绘画形态失之交臂后,则自然失去了介入纯艺术、纯审美创作的机会。尽管也有平面形式的漆艺存在,但这类作品起到的大多还是环境与器物装饰的功能,与真正的绘画艺术不可同日而语。于是,人们在谈到“漆艺”这个词时,想到更多的不是“艺术”,而是“工艺”。当然不得不承认,即便只是“工艺”,漆艺也着实令人叹为观止:在明代黄成所著《髹饰录》中具体撰述的漆艺技法就有一百余种之多,如果加以交叉运用所衍生出的技法则更为可观——时至今日,这个数字想必早已有了大幅增长。因此在传统的漆器制作中,工艺越繁复、制作越精细、材料越珍贵,往往作品的价值就越高,可以说这是典型的以“材”、以“技”而不是以“艺”作为评判标准的体现。
由此可见,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漆艺基本格局的形成,除了本体的自觉进化外,更无法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这当中有上层阶级见解、社会审美趣味的影响,也不乏技术进步、材料发明等等诸多机缘的出现。到了近代“山河已割国抢攘”的历史逆境下,漆艺虽然也有零星的发展,但这种服务于富有阶层、追求繁复工艺的传统艺术形式,在动荡中不可避免的陷入到了低谷。
二
新时期以来,中国漆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其中最靓丽的火花,莫过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漆画在全国美展上被确立为独立画种,从而完成了从“技”到“艺”的突破。
仅从“漆画”一词字面来看,这种形式是早已存在着的——除了上文提到的漆屏风以及器物表面的漆质彩绘,传统漆工艺中以单幅画面形式独立展示的工艺漆画,或许是最接近现代漆画的了。然而漆画真正从传统工艺领域脱颖而出并成为独立画种,其过程绝非一蹴而就。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芝卿、沈福文、雷圭元等几位早期的漆画先驱开始创作以独立画面形式出现的漆画作品,这可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漆画的萌创。如果说时局的动荡以及客观条件的制约,使得这几位现代漆画奠基者的创作活动未能形成规模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漆画艺术的不断发展,则为这一画种的最终生成累积了充分条件:1962年,“越南磨漆画展”在北京、上海两地举行,展览中磨漆艺术的独特魅力深深感染了观众,也使中国美术界产生了很大触动;在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国家派出人员专门赴越南研究、学习漆画——一定程度上看,越南磨漆画对于中国漆画画种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催发作用。资料表明,从六十年代开始直到“文革”结束前的数次全国性美术展览中,都不乏漆画的身影。到了1979年第五届全国美展上,乔十光先生的《泼水节》和蔡克振先生的《瓶中百合》两件漆画作品入选展览,其中《泼水节》一画获二等奖。到了八十年代初期,随着福建漆画展以及江西、天津漆画联展相继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可以说漆画在创作水平和人才储备上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最终在1984年的六届美展上以独立画种的姿态亮相可谓水到渠成。
从更深的层面看,改革开放之后,经过了对之前浩劫的批判和反思,文化艺术领域逐渐恢复起了正常、健康的审美活动,这一背景也为漆画画种的独立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回顾这一时期,无论是整个文化领域盛行的“美学热”,还是出现在美术界的“形式美”大讨论、现代美术运动等等,都折射出长期身陷狂热运动中的人们,对于清新而纯粹的审美生活的强烈渴求。从这个角度看,漆在艺术表现上的单纯性、概括性、装饰性,无不契合了这个时期的审美需求——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六届美展上展出的那些漆画作品:像《青藏高原》、《拉网》、《曝日头》、《窗口》、《一品红》、《春满钟山》、《鼓浪屿》等,无不充满着形式意味,在构图、色彩上都与传统工艺漆画以及越南磨漆画拉开了距离,具有现实与现代的气息;而在内容上,当时的漆画几乎很少有那种“关系性律动”式的主题性创作作品,这一点是明显区别于国、油、版等传统大画种。可以说,漆画画种在独立伊始就表现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特征:区别于传统、契合于时代。
由此可见,这一次由“漆”到“画”的现代转型,最本质的变化在于评判标准的改变,即从原来的“独具匠心、材美工巧”,转变为“气韵生动、意境深邃”等等绘画艺术的审美价值。当然在漆画的实际创作中,如果不对“漆”的材料工艺特征加以凸显的话,漆画往往无法展现其独特魅力并与其他画种拉开距离。可以说,漆画创作在材料、工艺上的复杂性是把双刃剑,工艺美术出身的漆画家往往会不自觉的将创作重心回归到传统工艺层面,在“技”与“艺”之间摇摆不定;而不少画家虽然对漆画情有独钟,然而面对略带神秘感的漆画材料和技法,常常又会望而却步。
实际上从绘画艺术的评价标准看,所谓的画面整体意境、格调等等,无非考量的是艺术家构思的精妙,以及艺术家能否运用材料、技法将画面主题、作者思想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从这个层面看,“技”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服务于画面主题、画家思想的。以中国画为例,写意和工笔作为两种画法可谓各具特点,但没有人会以工笔的繁和写意的简作为标准来判断二者的高低优劣,反而有些时候,一幅过度制作的工笔画会令人感到匠气十足,而一枝数叶、寥寥几笔,往往能够称神称妙、意境深远……同理在漆画艺术中,错彩镂金、繁复的堆砌或许能够造就一件优秀的漆器工艺品,但是过度的炫技往往也会使得作品忽略了主题、情感的表达,从而缺乏真正的艺术感染力。
一个成熟的画种,在题材表达上要有巨大的舒展性,在材料技法上要有宏大的包容性。一个成熟的漆画家,既要有绘画创作能力,同时要具备漆艺技法能力,二者缺一不可。而这正是漆画家队伍建设的大难题。当下中国漆画的创作主力主要集中于美术院校的设计系科内,他们在进行漆艺技法提升的同时,同样迫切需要绘画创作能力的引领;而具有相当绘画创作能力的漆画爱好者往往又难于获得系统学习漆艺技法的机会。这种两难局面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漆画的健康发展。由此可见,漆画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画种,确实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三
如果说以绘画的评判标准来看待成为独立画种的漆画,尚且还算纯粹的话,那么“漆艺”这样一个承载着七千年中国漆文化脉络的概念,显然更为复杂:它与社会演进、时代变革间不断发生着碰撞,而这些碰撞也直接影响着漆艺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的兴衰。
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工艺繁复、用料珍贵等因素,传统漆艺在历史上(尤其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长期脱离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统治阶级、富有阶层的玩物。这一状况直接导致漆艺的兴衰往往与时运、国势等外部因素联系在一起,即盛世兴旺、乱世衰落。新中国成立后,一切文化艺术成为全体人民共享的财富,传统漆艺也由此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然而这一契机的触发,却要更多的归结于政治与经济因素: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工艺美术产业(包括漆器产业)通过出口创造外汇财富,为支援国家建设、抵御外部势力封锁作出了特殊贡献。然而到了六七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传统手工艺被作为“四旧”而被打倒,漆器行业也未能幸免于难。再后来,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传统手工艺行业再一次为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独特贡献,漆器产业也迎来了一个迅猛却畸形的发展阶段:为追求产量和利润,不惜以机械化、流水线、代用品来投入生产——这些做法违背了漆工艺生产和市场的运作规律,也使得漆器产业在不久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遭受到巨大的冲击从而陷入新的低谷。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漆艺经历的起伏动荡丝毫不亚于之前的几千年,这当然与新中国历史上多次的转折变革密不可分。然而经过多次洗礼后仍能坚持并存活下来的,则是漆艺行业的骨干精英,理应成为新的发展阶段的火种与动力。
中国的事,确实存在着自身特有的行为方式。在那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年代里,讲究形式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抽象艺术则被作为形式主义而加以批判。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大潮般的涌入国门,抽象艺术非但不是洪水猛兽,反而被视为现代化的象征:君不见,一座座抽象形态的雕塑雨后春笋般的耸立在广场之中,起先是大城市,接着是中小城市,之后甚至到了集镇、村口。抽象艺术的大普及,给文艺理论界为艺术正本清源带来了难得的契机,重要的一点是形式语言被确认为艺术创作的本体因素。这个本体地位的确立,大大的促进了艺术创作形态的开拓,各种艺术形式都可以成为新时期艺术百花园中的一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漆艺理应找到一席之地。在相关有识之士的努力探索下,他们以中国大漆独有的材料和工艺特性,找到了一条以大漆的漆语、漆性、漆境营造出艺术意境的当代表达之路,创作形态则是漆立体、漆平面、漆空间,作品的关注点是将中国传统漆文化作新的时代穿越。这样的探索无疑应倍加赞赏和支持。湖北是中国大漆艺术的重要发源地,荆楚漆艺曾经为中国漆艺写下辉煌的篇章。进入21世纪后,湖北美术馆以“湖北国际漆艺三年展”的方式,为中国漆艺的振兴出力,既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又有人和兴旺的善果,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之喝彩。
值得一提的是,漆平面、漆立体能否与漆画、漆塑等同?应该说漆平面与漆立体、漆空间都是新创造的名称。为什么要创造新名?理由必然是与其对应的漆画、漆塑有不同的艺术追求,也就是有区别。如此说来,“漆平面(漆画)”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以学科分类看,漆艺人才的培养途径在设计学科的漆艺专业,而漆画人才的培养应该放在美术学科的相关专业和方向。在作理论阐述时,这个细节有时也是会影响大局的。
无论是传统的漆工艺,还是成为独立画种的漆画,乃至于今天涉入当代文化领域的现代漆艺,实际上都涉及文化形态与时代潮流的碰撞、对话。在当今的历史环境下,任何艺术形式都不可能延续以往单线条的发展轨迹,而是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状态。应当说,现代漆艺、漆画以及传统的漆器制作,实际上并不是某种演进或替代的关系,而是漆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碰撞的产物,并在当今共同成为漆文化体系中的重要部分。需要关注的是,现代漆艺作为三者当中与当下社会、时代背景关系极其密切的一种,无论它涉及怎样的文化命题,作为艺术形式的一种,它所具有的价值终将通过艺术的标准加以评判和展现——或许,这是中国漆文化一路走来并进入当代语境后,从业者们需要注意和警醒的一点。
2013年8月28日
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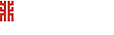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