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艺现代性的断想
陈勤群
如果说首届漆艺三年展的主题〝大漆世界―――材料、方法、精神〞阐明了一种如何面对传统艺术的清晰的文化立场。那么本届三年展的学术主题〝大漆世界―――源·流〞则展现了从母语出发,梳理历史脉络,实现当代转换的学术方向。
作为曾经的漆文化大国,漆艺在近现代是一种非常疏落边缘的文化活动。1936年郑师许先生的《漆器考》(中华书局出版);民国初各省的工艺传习所和学堂的漆工课程;1943年沈福文先生在成都首个重要的漆艺展,大约是近现代中国漆艺界在漆学术研究、漆工艺教育、漆艺术创作的最初纪录,也是中国漆艺现代性的最早萌动与先声。
中国漆艺在上世纪下半叶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两大历史进程:一是让漆艺从民间转移至高校成为一门学科,使文化资源建构成一种语言和价值体系,成为当代艺术和当代设计的一种形式语言,它关注的是漆语言形式的现代性。二是使漆艺从唯美和固步自封的圈子中走向思想和自由的批判,让漆艺从工艺美术转换成当代表达的一种方式,它强调的是用媒材演绎的思想者的素质,它研究的是漆语言观念的现代性。
进入新时期的中国漆艺界的每一个学术焦点的背后都有着文化思潮的根源,能从人们既不断追求创新、又不断地自我重复自我拷背中感受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种艺术潮流对艺术家的价值观、艺术观和表达方式的深刻影响。
上世紀未在形式觉醒、图式爆炸、材料实验的语境影响下年轻一代从不满足图式开始,纷纷寻找当代语言〝转换〞的突破口,于是作为学科和语言基础的材料,在漆艺现代性的第一个进程中分野了:有以大漆为主、其它材料为附的兼容派;有在传统技艺〝转换〞成现代绘画的语言时把母语都〝转换〞了的颠覆派;有只研究大漆创造可能性的母语派。
于是屈指可数的母语派与兼容派就注定要在大美术解构热潮的背景下,孤独求败地顽强坚守摸索,从架上、器型到空间,既要在纵向的比较中保持漆语言独特性的建构定位,又要在横向的对比中保持不断超越自我的解构状态。在建构与解构犬牙交错的纠結中,首先着力于中国漆艺在东方漆文化圈的话语规则中重新复兴和堀起。
漆艺在学术上也面临了从未有过的人数稀少却不断分化的困境:一方面对漆艺的不可替代性毫无认知,放弃了学科的逻辑起点,往消解自身的虚无主义方向滑动;另一方面又把所有漆艺的理想都倾注在日用品的润光上,在价值上往〝唯器独尊〞的本质主义方向张扬。漆艺正面临着以上左右两极的拉扯与震荡中。遂使中国漆艺界面临了一系列的现代性的焦虑:在工艺上追随邻国几十代人一个方向不间断努力形成的〝润光〞完美;在美学及形式上恶补西方百年现代主义的建构;在中国漆艺的系统传承转移和现代主义学科的建构还未提到议事日程时,后现代的批评家与艺术家们又纷纷登门或破门解构来了……。
漆艺既是个在数千年的婉延中在礼用、日用和艺用充分发展的古老艺术;又是一个在当代语境的思考和实践中未被充分展开的传统媒材,因为还未充分展开,人们对未知的东西总是充满幻想、主义丛生,更因为传统愈悠久,工艺愈庞杂,中国精神的“器”之观,愈容易被工艺的“器”之观所淹没。所以人们对漆艺如何发展:礼用?日用?还是艺用?等古代早已百花齐放并行不悖的基本问题上,作非此即彼等毫无意义的价值判断和争论,并对漆艺家提出源于自身的有限实践和理解产生的主观的导向,于是人们看到在拯救中国漆艺的诺亚方舟上,有着各种不同航向的主张在号召仅有的总数甚少的同一批漆艺家:时而划向东、时而飘向西,人们在众说纷纭的价值观和可能性中向各自的方向打转、摸索……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文化情景中我们在漆艺的材料、形态和观念的演绎上该作怎样的抉择?
或许所有传统样式都曾经面临关于如何抉择的共同困惑?漆艺与岩画、青铜、壁画、画像砖、画像石、剪纸、年画、陶艺、水墨等传统样式一样,贯穿其间的中国线造型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根据邵学海的研究中国漆画分蘖于漆画萌芽期的"纹间叙事",其后,彩绘与勾勒成为先秦与两汉髹饰的主体。宋、元、明漆艺的精华在雕漆、镶嵌与针刻,它们的线意识相当高古。明清各式描金漆画日益繁荣,并形成影响较大的四大版块:晋、闽、粤及吴越。如果沒有1840年的巨变,这个以线为主轴的各种材料的表现方式是个绵延数千年自成体系的视觉文化。
自鸦片战争开始渐渐输入了西方美术的一系列的书籍与思潮,留日留欧留苏留美,艺术与少年中国一样在寻找在新世纪中如何强国的种种主义与方法。艺术在救亡与启蒙的此消彼长中一直到文革的結束,才从它治回到了自治,八十年代的漆画运动正遇上新时期风起云涌的历史关头:上世纪末当国、油、版、雕在八五美术新潮的影响下,在短暂的时段中把西方现代主义近百年的艺术样式如饥似渴地借鉴了一番:从全因素的传统绘画样式的围城中出走,纷纷向单因素的实验方向解构。而此时漆画正向传统绘画样式的围城中进发,为获得全因素的绘画能力而努力建构,这种因画种发展历史阶段不同而形成的〝围城情境〞,使漆艺界对如何处理两大现代性进程中〝转移〞和〝转换〞〝解构〞和〝建构〞的问题时,相左的意见撞击的特别激烈,在毫无边界的研讨会上,人们往往会同时面对漆艺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不同话语与主张,喧嚣得让人无所适从。
众所周知当代视觉艺术经历了理论家所归納的形式的觉醒,文化的关怀,和样式的超越的三个阶段,当代艺朮发展到了样式的超越时,基本上传统的材料都逐渐边缘了,诸种思潮在前期解构的兴奋和后期观念的滥觞,使国、油、版在整个新时期都具有跨越材料的解构倾向,因各种媒材发展的历史时段的差异,对高度发展图式饱和的领域,解构是突破的催化剂,而在学科相当脆弱和幼稚的漆艺界,解构是把要命的双刃劍!
材料已经不重要,所以用什么材料也不重要,当90%的高校都不把大漆作为漆艺学科的材料界定和唯一的创造研究对象;当解构成为时尚这个画种这个学科就变得非常曲折了。在数十年短暂又动荡的历史背景下,当艺术先习惯于"它治",成为意识形态的奴婢;后又兴奋于"自治",陶醉于现代主义的重复中,人们以二三十年有限的个体实践和感受,轻易地取代了他人和历史的实践、感受与积淀,难以平心静气客观地面对数千年漆文化的浅溪深流回味勾沉、曲径通幽细细品鉴……。那个曾经使中国历代漆艺经久不衰的漆文化知音和精神贵族的阶层已云消雾散远离历史现场,文化的断层就无可避免了。
可以说对漆材料的彻底颠覆和变异,是以艺术的理由在漫长的漆艺历史长河中面对长驱直入的潮头蕩出的一个意外的小弯、一个历史的误会,它将以几代人迂回曲折的代价及经验潮起潮落后再回归长河。
在蕩出与回归的选择中、在欧风美雨前我们分化了:颠覆、解构、纠結、质疑、偏激、坚守、回归、认同、温厚者从"道不同亦相与谋"到"道不同不相为谋"、偏狭者直奔党同伐异了……充滿自由和大爱的艺术变得不自在不从容了,我们深深地陷入现代性的困惑中。应该说所有的学术焦点归根结底是个如何面对现代性的问题。
即使"现代"告別的是中世纪是前现代、是科学、民主、理想和自由匱乏的时代,这个迈向现代的告別,也依然充滿迷幻、困惑和痛苦,我们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接受西方百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前,还接受了西方写实主义至少有十七年,前后叠加对我们整个审美和教育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我们该怎样去面对具有礼用、日用和艺用多种传统的漆艺?怎样去面对漆画这样的一个传统的画种?我们的根系在哪里?我们既不能完全拒绝欧美日本、也不能放弃自身的传统唯东、西洋马首是瞻,……我们刚刚享受艺术自治的愉悅,我们又开始有了文化身份的焦虑。
张法的文化分析值得思考:按照汤因比《历史研究》的观点,统合希腊文明、中世纪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为一个统称为西方的文明,而非西方文明全世界有20个,在资本主义征服之前是各文明独自发展的分散的世界史,"在16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兴起,并向全球扩张,分散的世界文明史变成走向统一的世界文明史。"(张法 著《文艺与中国现代性》第4页 湖北教育出版社)现代性虽是告别中世紀开始萌芽的,但所有非西方国家在纳入统一世界文明史的过程,便是民族国家自身现代性漫长又复杂的开首和历程。统一的世界文明史是否也要有统一的艺术史,谁来书写谁来定义?或者说全球化是否意味着西方化,此老生常谈是所有非西方民族无法回避的问题,艺术界亦概莫能外。
朱乃正讲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油画进中国,油画改造了中国,中国改造了油画吗?”这种提问是很有意思的,应该说“油画改造了中国 ”它也正深刻地改变着中国漆画的面目和审美的趣味,无庸置疑它的影响在诸多方面都是有益的,但如果亦步亦趋地在表达方式和形态价值等都以油画为标准,甚至不惜彻底替换颠覆传统材料的属性,那堪称世界最古老的画种将名存实亡不复存在,漆画悠久犹如视觉的古汉语,它的文化气质、视觉特征正是用数千年的大漆传统来延续与呈现的,媒材的多样性正是保持世界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物质基础,当传统媒材成了边缘的少数派,那人们就有理由警醒与反思:它是否非得改造得跟油画一样,如果拒绝同化,那它的语境何在?它何以自立?
应该说〝转移〞在场的〝转换〞是大漆的漆艺;那么〝转移〞缺席的〝转换〞就是非漆的漆艺。而没有〝转移〞谈何〝转换〞?在此与其说是〝转换〞不如说是〝挪用〞显得更准确些,它仅挪其意而不用其实,它的意义和价值应该是观念性的非漆形态。
我们不是大漆的原教旨主义者,但我们警惕漆艺和漆画中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意义上的非大漆形态,我们关注与漆艺方法论有关的后现代意义上的非大漆形态:如隋建国的油漆作品:"时间的形状"和王光乐受传统漆艺寿棺的启发所作的丙稀〝寿漆〞作品。因为前一种非大漆形态是对漆语言形式现代性的遮蔽和误导;而后一种非大漆形态才是对漆语言观念现代性的有益启迪。
传统媒材的现代性进程就是不断地与各种思潮交融、激荡、辨析、梳理与建构的过程。上世纪未漆艺从工艺语言转换为绘画语言,产生了艺术意义上的〝漆语〞。装饰性和全因素是漆画界上世纪未首先展开的两大方向,装饰性未必仅走向唯美、全因素也不止于写实。图式语言、材料实验、书写性、意象化、图像的挪用与观念的表达等都先后成为中生代漆语所触及的新维度。作为架上形态这些维度在其它媒材中经过大量的作者参与、竞争、淘汰,并逐步形成了出类拔莘的高度,就此而言漆语的维度未必有多〝新〞,而只有具有语言不可替代性的〝漆语〞,才能在如云的架上形态中保持漆语特有的文化气质,才有可能成为有着数千年母语积淀的架上新维度,成为当代表达的中国方式,所以漆语言的不可替代性,成为漆语言形式现代性的重要表征。
不可替代性是人们观察漆语言形式现代性的重要切入点,而面对漆语言观念现代性,人们体察的就是作者的知识结构、文化自觉、志趣眼界、人文关怀、……
文本成为作者品位境界无可逃循的证据。但形式与观念之间并不是清晰的二元结构,观念表达的方式或者说艺术的方法论是中生代漆语突破的重点,漆艺最能体现〝层〞的语境,界外的王光乐其〝寿漆〞就深受传统漆艺寿棺的启发,但就层迭而言寿棺还不够极致,同样的厚度,尽管大漆簿髹要比油漆厚涂需要更多的禅心和更长的时光,不同之处是〝寿漆〞把物化了的时光以清晰的色层纯粹地呈现,裸露成一丝丝心迹与时间流淌的混合物,形式即内容、方法与观念混然一体了,而传统漆艺千百层髹饰的禅意容易被装饰的唯美、工艺的炫技和日用的机心遮蔽了,类漆的泛滥正是对毫无艺术感觉的炫技派的惩罚与反拨。
同为东方漆文化圈的漆艺界面对西方都有一个在艺术创造中如何吸收文化资源、厘定文化身份、纠结于东方主义与世界主义二元论争等诸多问题。表现相同的艺术媒材在不同的国度中如何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而无论东、西方的漆艺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命题:就是如何使古老的漆语言成为当代艺术的一种表达方式,或者说滋生出N种表达方式。而本届三年展正是当代思考的最新呈现。
近十年来漆艺界"绘画性"的提出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焦虑,是一种现代性的焦虑,当代艺术对所有的传统样式都形成了一种压力,"当代"是许多传统样式的守望者努力争取的状态,尽管当代艺术也是有困惑的,至少中国的当代艺术有两个学术表征在审视着实践者:一是直指当下,二为终极关怀。
纵使你具有"心事浩荡连广宇"的胸怀并有足够的艺术张力,但语境无法具有没有边界的无限度的批判性,结果最终不是在观念自律和语言演绎的维度上寻找平衡点,就是直接选择规避当下问鼎终极。
尘世喧嚣魂不守舍,人们日益疏于同情体贴、无法想象终极、难以关怀大爱,远离"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而超强的艺术穿透力,才能够天荒地老依然生效,尽管此类大作已很难出现了,但总有人发自內心不倦思考不断倾诉无关成败,它依然是一种西斯弗斯式的生存方式。
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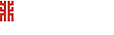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