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勇《在“大漆世界:时序——2016湖北国际漆艺三年展”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在“大漆世界:时序——2016湖北国际漆艺三年展”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颜勇
首先感谢湖北美术馆和皮道坚老师、张颂仁老师、冀少峰老师邀请我来到这里与大家一起学习。我对漆艺没有太多研究,但是确实非常喜欢漆器,尤其喜欢楚文化中的漆器,而且也很希望知道楚漆器以及其他伟大的传统东方漆器工艺遗产在当代艺术与工艺语境中得以传承的现状以及可能性。因此对我来说,能够来到这里参观这次展览、参与这场研讨会,确实是非常幸运。
我想先从这个展览的主题——“时序”——谈起。我觉得这个概念用得非常好。人类对时序的感知是一种共性的东西,东方与西方并不存在差异,但感知的方式却似乎不太一样。
在西方,早期的时序观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中有一段描述格劳科斯(Glaucus)与狄奥墨得斯(Diomedes)在战场相见,狄奥墨得斯问对方家世,格劳科斯回答说:“正如树叶的枯荣,人类的世代也是如此。/秋风将树叶吹落到地上,春天来临,/林中又会萌发,长出新的绿叶,人类也是一代出生,一代凋零。”这个比喻可以说是开启了西方人将事物兴衰相比于时序更替的一种模式。我为什么要用“模式”这个词呢?因为只过了几百年,在古典时期,柏拉图的《国家篇》(Politeia)中就借苏格拉底之口用类似的方式来解释政治制度:“一个建立得这么好的国家要动摇它颠覆它确是不容易的;但是,既然一切有产生的事物必有灭亡,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当然也是不能永久的,也是一定要解体的。情况将如下述。不仅地下长出来的植物而且包括地上生出来的动物,它们的灵魂和躯体都有声誉的有利时节和不利时节;两种时节在由它们组合成环满一圈时便周期地来到了。”柏拉图接着甚至使用一些数学原理的来说明这种神圣的周期。我们知道,《国家篇》同时也是西方文艺理论的经典著述;这种兴衰周期论跟美术史非常有关系,因为它后来形成了西方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传统。在16世纪,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所撰写的那部西方第一部艺术家传记与艺术史著述就是以这种兴衰周期论为基本论调,认为艺术的发展是从初生逐步改进直至臻于完善的过程。西方人的时序观与相应的艺术发展观念——我们不管它对还是不对——似乎是这样的:人们在谈论艺术或者是谈论各种自然事物的时候,是一个外在的观察者;对象就是对象,主体就是主体,主体外在于艺术或者自然现象,然后去观察它。
东方有没有类似的观察方式或者艺术史观?当然有。只要是人类,都会有对时序的观察和感受。刘勰曾经用与柏拉图、瓦萨里类似的兴衰周期论讨论文学。《文心雕龙》里就有一篇《时序》,里面有一句话:“文学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是与柏拉图、瓦萨里类似的兴衰周期论。不过,中国的时序观与西方是不太一样的。可以和荷马史诗形成非常有趣的对应的,是中国的楚辞。楚辞和楚漆器都是楚文化的重要代表。宋玉的《九辩》大家非常熟悉,开篇就说:“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大概意思是秋天实在太悲凉了,草木飘落下来,让人感到很伤感。这并不是一个观察的角度,而是一个感受性的,感悟的角度。其实就算在刘勰那里,也是以感为主的。《文心雕龙·物色》写道:“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是在说诗人是在感悟自然,诗人对自然的描摹是用心去“徘徊”,用心去感受自然:最强调的显然不是“观”,而是“感”。我们观看楚漆器或者其他东方传达的漆器上的装饰纹样,还有那些结构造型,等等,通常不会发现了什么很清晰的具体的对象化的东西,而是往往莫名其妙地感到了某种空灵的意境。
我并不想说西方文化中没有“感”或者是东方文化中没有“观”——二者都在中西方文化中都存在着。不过,就东西文化史、思想史发展的总体脉络而言,确实相对来说西方是以“观”为主,东方是以“感”为主。这两种方式,一个是观察的、理性的、分析的,关注外在的对象世界,另外一个是感悟的、诗性的,重视自我精神世界。关于中国古代各种艺术类型,包括漆器,我们时不时地听到“君子不器”之类的说法,还有对“玩物丧志”的批评,其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可能都与这种思维模式有点关系,因为东方人似乎不太习惯把物当成是纯粹外在于人类的对象。当然此二者并不存在价值上的高低,不过东方文化在总体上确实是更精神性的,更去物质化的。
东和西的这两种倾向在近代发生了碰撞,而且对东方绝大部分国家来说,这个碰撞的直接结果可能并不是一种在平等意义上互补与合流,而是舍弃自己的精神感悟的方式,接受外来的那种将事物客观化的、观察的方式。在中国,这种转变大约是发生于清末民初。
我们知道,1862年清廷设立了同文馆。同文馆是洋务派倡导设立的,不过在1862年洋务派与保守派的冲突还没有那么明显。他们的冲突是什么时候变得白热化的?是在五年后,在1866年奕䜣等洋务派官员奏请在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人员的时候。当时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极力反对,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们跟洋务派轮流上奏,反复争论。不过同治朝还是比较认可奕䜣的意见。一般认为这场争论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似乎很少人留意到它跟近现代以来中国工艺观念衍变与设计学科建立的关系。在同文馆里研究天文、算学,其实就是真正地把外在的“物”客观化然后进行研究,而同文馆发展这种研究的目的,其实就是要研究制作先进武器军备的技术,这就不能不涉及工艺与设计。因此与天文学、算学一起,设计学实际上比绝大部分现代学科都更早地在中国官方教育体制中出现的新学问。很显然地,这种新学问的导向是远离精神的,偏向物质的。
后面发生的事情大家都非常熟悉:1894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公车上书;1898年,戊戌变法,然后戊戌政变;1905年,中国科举制度被废止;1912年,清亡。让我们看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关于工艺教育谈论过些什么。1894年春,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不久,郑观应刊印《盛世危言》,里面有一句话:“中国才智之人皆驰骛于清净虚无之学,其于工艺一事简陋因循,习焉不察也久矣!”他在感叹中国人几千年来老讲究精神感悟,对具体的对象化的工艺制作却漠不关心,只会因循守旧,然后各种工艺就越来越简陋。其实这个说法未必妥当,不过我们先不管它。在1904年,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物质救国论》,说“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然。方今竞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这回是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你想活下去,就别玩什么精神感悟了,先搞好物质学再说。然后到了民国初年,蔡元培从德国归来,推行美育;美育当然更多是与精神世界相关,不过这马上就遭到了一些批评。当时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的主编陆费逵针对蔡元培的意见,撰写了一篇文章说:几千年来,中国教育就败在太过讲究“出世之观念,优美尊严之感”,现在我们民国建立起来了,还讲什么美育?应该倡导实利主义教育,让人人通过教育都获得谋生技能,能够自食其力。这种议论当然也有其合理之处,不过我不太相信一个仅仅为了谋生而工作的漆艺工匠能够制作出某种像楚文化漆器那样的令人产生强烈精神震撼的器物。
不管怎么说,就是在人们普遍崇尚物质学的气候中,传统的工艺学一步步地演变为今天的设计学。搞中国近代美术史的人喜欢提清末的“图画手工科”,说那是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开端,其实这说法不准确,因为“图画手工科”包括“图画”跟“手工”,二者合起来指向的是与康有为所说的“物质学”相联系的东西,跟美的艺术(fine art)反而有点远。当时还有“意匠图绘”的提法,这个“意匠”是从日本人那里借用来的对译英文design的术语,大致就是“图画手工科”中的“图画”。然后在20世纪10年代末,design的另一个同样是由日本人翻译的汉字译名“图案”也日益流行起来,一些美术院校,例如国立北平艺专、杭州国立艺术院,开设有图案系。然后像陈之佛、雷圭元这样一些名字就在近代美术史、设计史上出现了。意匠也好,图案也好,日本人用来指称西方design的时候,着眼点主要还是作为商品的对象,艺术性、美感这类东西主要是为了促进消费行为。20年代末之后,中国人又渐渐习惯使用“工艺美术”一词去理解design,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不过对此我们今天没法多谈。我现在想说的是,我相信借用西方design的视野或者思路去重新审视东方传统工艺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这不代表放弃传统工艺中的一些核心的东西然后移植一些西方现代的东西就算是告别了落后的传统进入了先进的现代。我一点也不认为传统与现代是二元对立的东西。
我还想粗略地提一下东方漆艺在西方现代文化史中的存在状态。刚才Margarete M. Prüch女士和Patricia Frick女士都很细致地介绍了前现代的中国漆艺在向西方传播的情况,作为西方学者,她们对漆器的认识与研究水平甚至超出国内许多专家,至少我自己非常受教。Patricia Frick女士刚才谈到了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漆器的喜爱之情,我觉得从东方漆艺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关系来看,18世纪有一个Patricia Frick女士似乎不太关注的现象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在当时中国风情(chinoiserie)时尚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漆器流行开来,并且越来越不局限于宫廷而成为面向多元阶层的商业销售品。18世纪伦敦家具设计师齐彭代尔(Thomas Chippendale)的漆艺家具应该是典型例子,他不仅在家具中大量使用漆艺与中国塔、龙之类的装饰等元素,而且在1754年还出版了一本自我销售的图录,叫《绅士与橱柜制造者指南》(the Gentleman and Cabinet Maker’s Director),我们从书名就知道,这册子不仅仅是给王公贵族看的。一百多年后康有为流亡到欧洲的时候不知道有没听过齐彭代尔的名字,但齐彭代尔式的家具他肯定见过,他应该会将这种采用东方漆艺的家具视为“物质学”的一部分。我相信齐彭代尔所采用的销售策略是一种民主化的征象,也是漆艺这样一些精美的传统工艺进入现代社会的必经途径。不过此时漆艺进入现代文化的途径与其说是艺术的,毋宁说是社会的。
漆艺第二次跟现代语境打交道要归功于艺术与工艺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和唯美运动(Aesthetic Movement),这回就真的跟艺术有关系了。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圈子似乎并没有非常擅长漆艺的人物,但他们喜欢各种传统手工艺,讨厌机器。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将这个情况放大成他们更接近感性的东方传统、更偏离理性的西方传统,当然还有很多可争议的空间,不过考虑到艺术与工艺运动对后来的设计文化上几乎无所不在的影响,它确实也为各种传统工艺进入现代设计语境提供了契机。至于在唯美运动那里,漆艺本身大概就已经代表了美。在惠斯勒(James Whistler)的那个著名的“孔雀房间”(The Peacock Room)里,爱德华·戈德温(Edward William Godwin)就在家具中使用了漆艺。不过总体来说,漆艺之美是很边缘化的,而且并没有真正地内化成为现代艺术的一部分。
把传统漆艺内化成为现代艺术,大概是从装饰风艺术(Art Deco)开始的,所以刚才Heri Gahbler先生介绍欧洲当代漆艺要首先从法国设计师让·杜南德(Jean Dunand)的漆艺说起。更早一点,在1905年前后,维也纳制造工场(Wiener Werkstätte)的卡尔·泽茨卡(Carl Otto Czeschka)可能也已经在探索漆艺在现代装饰艺术中的应用了。1920年代法国的装饰风艺术当然是最引人注目的,杜南德的漆艺尤其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精致奢华的美感。张颂仁老师在为这次展览撰写的文章提到漆艺中“皮相”与“奢华”感的关系,像杜南德这样的艺术家可谓深谙个中三昧。但是我们知道,在现代主义艺术文化中,装饰风艺术的处境有点不尴不尬。一方面它跟立体主义和野兽派关系密切,并且跟风格派、构成主义、包豪斯等互有借鉴,但另一方面又常常被各种现代主义运动视为落伍的代表、批判的对象,例如勒·柯布西埃(Le Corbusier)就批判它是“对机器现象的反抗”,是“临终的抽搐”,“垂死的事物”。事实上,在一般现代美术史或现代设计史的著述中,你很难找到跟漆艺有关的段落。这种尴尬局面恐怕是要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所谓后现代文化兴起之后,才会有缓解的机会。大家厌恶了标准化,厌恶了单元世界,厌恶了过度理性,然后就要重新发掘有多种可能性的传统,看这些传统有没可能成为当代文化的一部分充满活力的血液。我认为这就是Heri Gahbler先生所介绍欧洲当代漆艺发展的主要背景。
如果从齐彭代尔时代算起,到今天,漆艺在西方现当代文化中至少存在了两个半世纪以上。它可能曾经很边缘化,但始终有个位置,而且今天这个位置似乎越来越受重视。我想对东方国家的漆艺家们来说,这肯定也是一个风水轮流转的机会,这次漆艺展览的当代作品清晰展示了他们的创作活力。这个展览本身很多元,有些展品是很“当代的”,有些展品是很“漆艺的”,有可能会因此而引发一些批评,但我觉得它反而更清晰地展示了当代漆艺文化的复杂性。当然我对当代漆艺没有什么发言权,但在参观展览之后,确实感到了一种在当代艺术语境与传统工艺文化之间的一种微妙张力。我不知道当代漆艺是否应该刻意强调自己的“当代性”地跟传统拉开距离,又或者应该尽可能地重新返回东方传统那种凭藉技术上升至精神世界的古典境界——“技近乎道”,但我觉得这也许并不太重要。当代世界应该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当代漆艺也就不妨多元一点。也许重要的是漆艺作品能否产生某种力量,以获得观者的共鸣,让观者用观察的或者感悟的或者二者兼之的方式,去欣赏或批评每一件具体的作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应该感谢这次展览。
(本文系据现场发言录音稿与发言提纲整理而成)
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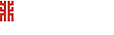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