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85
沈伟
“回望’85”,是为2007年度在武汉举办的“第二届美术文献展”策划的一个特展主题。
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美术最为重要的现象,“新潮美术”、“’85思潮”、“青年美术之潮”等等,均表征为一个共同的话语对象,而“’85美术运动”概念的明确提出,则来自高名潞1986年发表于《美术家通讯》第4期的《’85美术运动》一文。
自上而下的“解放思想”,是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得以展开的一个时代背景。在这个时期里,风起云涌于各地的美术群体及其运动性的“思潮”,使得中国美术的理论和实践都突然具有了“突变”的态势。就艺术史的角度而言,“’85”概念,既指向一个具有特定社会内涵的时段,同时,它也指向中国现当代艺术转化过程中的一种具有特定价值倾向的观念方式。事实上也是如此,在目前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著述中,“’85美术”一词,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中均能获得不同层面和角度的丰富蕴意。
本文无意就中国的“’85美术思潮”作全面而完整的评价,但是,借“文献展”之际,以湖北的地缘关系,回望并审视二十年前现代中国社会整体观念变革之中的那一场“视觉革命”,在整体性的运动特征之外,我们似乎更能够体会到某种区域性文化的独特性格。
《美术思潮》
1984年10月,周韶华以湖北美协主席团的名义宣布由彭德主持创办一份美术理论刊物。1985年1月,经过酝酿和筹划,以《美术思潮》为刊名发行试刊号,4月正式出刊,原计划为月刊,年底以后又改为双月刊,至1987年底被迫停刊时的第6期终刊号,前后编辑三年,出刊22期,总印数近30万册。创刊之时,彭德任主编,副主编为鲁慕迅、周韶华,编委有皮道坚、陈方既、刘纲纪,编辑部主任戴筠。1986年底调整,皮道坚为副主编,严善錞为编委,鲁虹为编辑部主任。
从前一个时代凝滞的思维定势中走出,八十年代的中国美术界,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一个极其鲜明的特色。艺术家与理论家们在特定的文化与思想背景中共同思索艺术的价值与走向,从而也促成了理论的先导意义。而在此之际的“美学热”、“哲学热”、“文化学热”等等思想热潮的相继兴起,则充分显示了美术的“思潮”所能形成的前提。
《美术思潮》是应运而生的,作为一个现代型的美术理论刊物,它力主探讨与争鸣,并尤其显示出对年轻一代富于锐气的思维的宽容和鼓励,因此在创办伊始,它就在中国美术界激起波澜。就刊物本身而言,我们在诸如“观点鲜明”、“方式灵活”、“富于思辨”等等的特色之外,还可以继续分析出它在当时更多新鲜的创意,但是所有这一切的根本,是彭德在《美术思潮》第一期“答客问”中所宣告的:“以推倒现存的教条和建立新的理论为己任”。这无疑是对长期以来空洞乏味的体制内艺术及其理论基础的蔑视和冲击。“一些有朝气,有才智、有锋芒,有远见的美术青年不是被埋没就是被异化。《美术思潮》强调刊物的青年化,正是试图打破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然而勇气的凸显并不意味着方法的实现,作为一份敢为天下先的现代美术理论刊物,《美术思潮》的明确立场,就是“将不遗余力地给这一代美术理论家提供阵地,并从他们身上寻找出路”。
检索《美术思潮》的编辑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除了编辑部的彭德、皮道坚、严善錞、鲁虹、祝斌等人,编辑部之外的栗宪庭、杨小彦、黄专、邵宏、李松等人,也先后参与并主持了《美术思潮》的编辑。在《美术思潮》最后一期的最后一页,我们还可以注意一份“部分重点作者名单”,其中有:郎绍君、水天中、高名潞、刘骁纯、刘曦林、索菲、王小箭、贾方舟、范景中、王林、殷双喜、张蔷、邓平祥、李小山、陈孝信、朱青生、费大为、邹跃进、陈丹青、丁方、陈云岗、王广义、舒群、张培力、黄永砯、李路明、王川、尚扬……实际上,我们不妨把这一页看作是’85之后一个新的批评时代的开端,因为这一串名单所显示的,正是此后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活跃力量。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美术思潮》是在’85美术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家集中演练并迈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摇篮。那是一个纯粹的批评时代,是一个着力追求艺术的社会学意义的时代。尽管这些批评的思绪,往往超越并大于了艺术的本身,但是,在中国美术界激情燃烧而又充满着迷惘和困惑的时代,《美术思潮》与其他少数几个精神相通的刊物一道,共同担当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启蒙”。
1986年底,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专文推介了大陆美术界的“两刊一报”,即《美术思潮》、《江苏画刊》和《中国美术报》。1987年底,在终刊号的《蓦然回首说思潮》一文中,彭德以编者的角度归纳了刊物的几个主要特征:倾向性、青年化、非名人化、非区域性,并藉此针对芸芸刊物中的那种“没有追求、没有个性、没有表情的东西”。
一份刊物的价值,是不会因为其曾经有限的生命的终结而被人们遗忘的。然而有意味的是,彭德当年所批评和否定的那些“东西”,恰恰在今天泛滥的艺术(美术)出版中比比皆是,而当时他所针对的种种理论界的“不正常的状况”,也并没有因近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和艺术的开明而结束,在此意义上讲,“继续革命”的呼声,仍然是有理由的。
湖北青年美术节
郎绍君在1986年12月29日《中国美术报》第一版的湖北美术专版上撰文说:“湖北青年美术节是国内迄今最大规模的现代美术群展。它的作品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并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它的组织形式、宽松的民主氛围,给人以深刻印象。”确实,“湖北青年美术节”是’85时期湖北现代美术群体运动的整体亮相,在“理论先行”的氛围里,湖北的艺术家们在艺术实践中显示出了“超越’85”的企图。
与当时各地青年美术群体的民间活动方式不同,“湖北青年美术节”是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美术群体的盛大集会,经过美协湖北分会的前期策动,并得到省、市级政府和省委宣传部的支持,1986年10月底至11月初,各种“自寻场地、自选作品、自己布展”的各群体美展在武汉、黄石、沙市、襄樊、十堰等9个城市同时登场。据当时的统计,28个展场、50多个群体和个人展的2000多件作品在同一时间里被推向了公众,其中,仅武汉市青少年宫一处的“艺术游园”活动,就集合了22个展览。
美学家刘纲纪先生在发表于《美术思潮》1987年第1期的长文《走向现代:湖北青年美术节部分作品观后》里给出了一个正面的肯定:“这次青年美术节的举办,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创作自由和艺术民主的一次生动体现,是改革在艺术领域中结出的果实。”
这些“果实”是来之不易的:
湖北美术院绘画雕塑展(1986年11月1日,湖北省美术院展厅):傅中望、黄雅莉、未明、严善錞等11人。
JL群体展(1986年11月1日,湖北省美术院展厅):刘子建、吴国全、陈运权。
圆房子画展(1986年10月28日,武汉青少年宫):仇帝、王心耀、孙绍群、高鸣峰、肖丰、王祥林、郭润文、李建生等8人。
画展(1986年10月28日,武汉青少年宫) :王用家、吴国阳、胡朝阳、王白焦、夏子仪、杨耀州、陈建刚等7人。
流星画展(1986年10月28日,武汉青少年宫):林玮、仇修、叶军、黄邦雄等4人。
方舟艺术群体(1986年10月28日,武汉青少年宫):吕墩墩、尹光等19人。
直线方块画展(1986年10月28日,武汉青少年宫):张亚席、刘成春等人。
版人画展(1986年10月28日,汉阳晴川阁):张广慧、王涌、邵学海、刘明。
艺友画会作品展(1986年10月28日,江汉工人文化宫):冷军、杨继东、宫建中、岑龙、蔡卫东、谢逢春、江中潮、沈飞、燕柳林等9人。
红色通道画展(1986年11月1日,武汉大学行政楼底层大厅):肖丰、吴国全、罗彬、宋叶中等4人。
三心二意作品展(1986年11月1日,武昌起义公园抱冰堂):陈研、吉厚明、左正尧、罗莹、杨国辛等9人。
从人美术作品展(1986年11月1日,原武汉展览馆):吕唯唯、谢鸿辉、刘明、吕墩墩、孔可风、朱惠娟、桂美武等人。
青年美术节之后,由于在美术界激起的效应,1987年4月24日至5月9日,经中国美协书记葛维墨的推荐,湖北分会挑选了一部分精品,与中国美协在北京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了“湖北青年美术节作品选展”。而在青年美术节之前的1985年初,武汉成立较早的“艺友画会”部分画友就已在原武汉展览馆以群体展的面貌正式出现了。1985年6月,肖丰、吴国全、罗彬、宋叶中四人的“大学圈画展”,也在武汉大学行政楼底层大厅顺利展出。湖北青年美术群体的兴起,不仅同声相气于全国性的美术运动,它更直接地受到了《美术思潮》的影响与激励,乃至于有评论说:《美术思潮》的生气与激进“常常被看成是湖北美术界的形象”(吕澎)。
生气与激进是源于现实的。尽管“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氛围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延续的“现代性”追求,促成了八十年代中国美术的启蒙,但长期以来的体制内艺术的单一与乏味,却使得许多的艺术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对抗的方式来极力改变艺术原有的形式与观念,并朝向艺术的“主体性”方向显彰。在此之际,美术已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视觉图像,在当时,美术家们同样担当着思想者的历史使命:社会学的批判、哲学和文化的维度、功能性的追求,甚至是艺术的“图解”。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短暂的一个时期内所复兴的西方现代艺术的引进与改造,又往往使得艺术家们按捺不住形式感的饥渴与表现性的企图,因此他们尚未来得及真正地深入到艺术的价值层面。与理论争鸣和探讨的人文学科的支撑相比,新潮美术运动在艺术的实践上就显得仓促而甚至落入空泛。关于这一点,严善錞在1986年12月29日《中国美术报》发表的《青年美术运动的反省》一文中曾有过敏感的反应。针对湖北的青年美术节,他以“我们的艺术创新是以西方现代艺术作为背景这一前提”,归纳了四个方面的缺陷,如:展览缺乏总体设计、对传统研究不够、艺术语汇不够单纯、艺术层次尚欠丰富。
实际上,相比于我们今天日趋商业化了的“当代艺术”,’85时期的艺术是纯粹的,也是有“内容”的,从外部向西方现代艺术学习,只是为了找回自身艺术状态的一个自然过程。因此无论如何,“湖北青年美术节”的意义,并不在于当时的作品乃至于展览本身,而是在于它作为一个“事件”所留下的激进和救赎意识。再从全国的范围内来看,“湖北青年美术节”以大规模的集结,并甚至作为“官方”的活动而推向艺术界的前台,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青年美术群体在北方、西南、西北以及东南沿海等地游离于民间,并且活动分散的印象。湖北的“现代派”美术被激荡得生机勃勃,而武汉这个中国中部最大的省会城市,也在转瞬之间具有了现代艺术“中心”的凝聚力。
部落·部落
紧随青年美术节之后,“部落·部落”又成为了一个具有递进意义的重要群体。
1986年12月20日,“部落·部落第一回展”在湖北美术学院展厅开展,这是一个以湖北美术学院青年美术教师为主体的现代艺术展,参展者有15人:魏光庆、曹丹、毛春义、田挥、陈顺安、李邦耀、何立、方少华、郭正善、冯学伟、谢跃、董继宁、孙汉桥、范汉成、李微。在当时的文化史理解中,“部落”的概念,或许包含有人类童蒙时代的向往,它意味着阶级产生之前的“无为”状态,也意味着一种理想化的乌托邦精神。如同当时所有的青年美术群体活动那样,“部落·部落”展也发布了一个宣言式的序言,在玄奥的《新约全书》中摘引了一段著名的“马可福音”,引申而言的意思是:“具有主体精神的艺术家并不等于一粒被先天因素决定了的种子,他的命运,要取决于他在艺术观上的选择。”
作为“艺术观”的代言人,彭德在《当代画坛第四批种子的隆起》一文中为这批作者进一步解说了他们的价值取向:“‘部落·部落’”群体的选择是理性化的选择。他们不同于’85美术新潮的弄潮儿,更多地借用美术的手段去表达一种文化的态度,去激烈地抨击传统美术的僵死模式,而是平心静气地在那里探索他们所感兴趣的艺术。他们不想成为艺术运动的倡导者,尽管他们肯定倡导活动的意义;他们感到关注运动只是关注文化冲撞的高潮期,而高潮的到来意味着退潮的开始。”什么是“艺术”,在今天恐怕已经越来越说不清楚了,而在当时,它却明明白白地是一种改变自我与社会的态度和事业。
“部落·部落”的同仁们一共展出了80余件作品,在形式上包括了油画、水墨、雕塑以及现成品。确实,与青年美术节期间大多数群体五花八门的“热闹”不同,这个展览显示出整体上的冷静,并在大多数的作品中流露出了省思的气息。在表现、象征、甚至抽象等等的类型中,“部落·部落”对各种现代艺术流派的尝试,也带来了风格的多元,由此也与人们记忆中所厌倦的一元化美术模式形成了对照。值得注意的是,“部落·部落”的作者并非都是学院中从事纯艺术的绘画系教师,而大半来自于当时的工艺系,从这一点上,我们或许更能够体会到在那个时代里所有接受过艺术教育的年轻一代对于潮流的热情和投入。然而,“新潮美术”作为一种“运动”的宿命,在现实认知的理性中必将有所意识,这就使得这一过程之中的艺术选择显得尤其的沉重。而且也正是因为如此,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那种为艺术而痴迷、为使命而奉献的宗教般的情绪,并由此备感艺术的圣洁。
以上所论,只是在“回望’85”特展的策划中对于三个主要线索的管窥。
八十年代中期,湖北的青年美术思潮在某种意义上是理论催生的结果。具体而言,湖北的理论群体,尤其是《美术思潮》将自发的群体运动导向了理论上的思辨气质与实践中的先锋精神。
不言而喻的是,’85美术运动对于当代中国美术界的冲击,具有着战略性的意味和文化变革的功利性目的。就个体意识与社会惯性相对的历史情境而言,群体行为是艺术家们在当时凸现思维倾向和价值选择,并相互增强信心的一种有效方式,而一旦“启蒙”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的两个方面均获得了一定的成效,环境就将对艺术的本身提出新的要求。于是,1987年以后,艺术的“实验”仍在继续,而美术圈子里抱团的现象遂趋于平淡,群众运动式的盲目冲动也就逐渐消失。
历史总是具有反讽的意味,九十年代以来的商业化之后,“先锋”的思维却从另一个方向被种种无形的力量重新一统化,从而造成中国当代艺术在市场中的沉沦。仅此而言,对’85的回望,无时不在历史的局限中反映出思想解放的意义,并显现价值角度的纯粹意识及其潜在的永恒性。
诚如福柯所言:“批评的作用,应当呈现于冲突与对抗的过程中,它是拒绝性的尝试与努力。”也正因为如此,回望’85美术思潮的沉淀,它应该被看作是至今为止的中国当代艺术进程中弥足珍贵的精神之源,而不仅仅只是一种历史的记忆。
2007年8月于湖北美术学院
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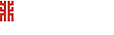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