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中的20世纪湖北美术:关于以武汉地区为中心的美术文献梳理
艺术史中的20世纪湖北美术:
关于以武汉地区为中心的美术文献梳理
沈 伟 湖北美术学院教授
20世纪后半叶以来,美术史研究以视觉艺术理论与方法的提升而成为一门人文学科,并介入人类生活历史图景的复原或重构。另一方面,也正如上世纪中期(英)历史学家科林伍德所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样,新的历史研究,又往往会以全新的问题意识与价值观念来审视和阐释过往的事实与经验。而就现实的经验而言,正在发生和发展着的新的艺术实践成果,则会直接地以当下的思维惯性影响到人们对于艺术传统和遗产的判断与选择。缘于此,艺术史的梳理,由于艺术创作研究对象的客观状况与主观判断的相互作用,而成为一项富于挑战性的工作,尤其在当代艺术史的研究中更是如此。
20世纪的湖北美术(以武汉为中心的梳理),无疑是中国现代艺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不仅是因为湖北的美术,在一个世纪的纵横发展中,留下了一连串可圈可点的事件、人物与成果,也更因为湖北武汉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巨变中所曾占据的显要位置。“刊石纪功,图像存形”(西晋﹒卫操),此际的美术实践活动,恰恰是从图像历史的角度,鲜活而丰富地印证了这一风云际会的时代变革的脉络。
文献性质的美术史梳理,目的在于对美术实践的历史过程形成接近客观状况的认知和理解,而在这一过程中,无论采用何种的方法与角度,史料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一般意义上,史料涵盖了生活实践的历史中所能遗留的实物和痕迹,而对于美术史建构所涉及的史料,除了直接遗存的美术作品的物质性成果,也包括了图册、书籍、报刊、档案、书信等文本资料、与美术活动和事件构成关系的遗留物品、乃至在相关人群的口耳相传中所保留的口述史料。20世纪湖北武汉的美术,虽然有着印象之中的丰富和深沉,但却未见有过自觉意识的整理,因此也未形成系统化的沉淀。
目前,以湖北美术馆的“百年纵横——20世纪湖北美术文献展”为契机,通过数年时间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广泛的史料搜集和甄别,也通过对于如以上所述材料范围的综合、比对与分析、提炼,初步可以形成20世纪湖北美术的演进与发展的基本线索。
或可试说一二如下:
例如民国时期的美术,就较能体现史料钩沉的作用。
民国之初,随着“大武汉”的成形,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共同汇聚为“汉上”的地域性概念,并以地理通衢之优势吐纳南北,吸引了当时期国内文化与艺术界名流们的频繁过往。而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的转型,以往美术交往活动的传统私密(雅集)性质,开始向现代信息化方式的公众性领域延伸与扩展,相关的美术家聚会和美术作品的交流与展示,不再局限于私家的馆阁之中,而是移向大众性质的公共场所,如校舍、银行、商会等等。同时,在这一时期,不论是官方的、或是民间的美术活动与展览,大多会借助于当地的各主要报章,公开地发布启示和广告。
因此,尽管民国时期美术因时代相隔,取证不易,直接性的文献留存匮乏,但全面检索十数种完整的地方报章,并参以相关机构所保存的档案材料,以往的片段痕迹,终究能够被连缀而形成活动事迹的编年。而通过史料的钩沉,当时期地域美术的状况,包括美术家事迹、美术社团活动、艺术知识传播、创作理论争鸣、外埠艺术家的交流往还,乃至于几近湮没的画家人物、艺术经济活动、绘画市场状况,均能由此而管窥一斑。
而民国武汉的美术教育,则与中国社会和文教的现代化进程相呼应,成为最早进入现代形态美术教育的重镇之一。从清末洋务运动在汉所办的实业学堂,到20世纪初开始兴起的一般性工艺学堂、传习所、函授学校,到20年代“私立武昌美术学校”(后立案更名为“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的正式创办,众多的官学与私学,均在地方文献中留下了丰富的印迹。即以“武昌艺专”为例,通过文献资料的完整梳理,以及相关历史实物和作品遗存的征集,从其办学宗旨、招生方式、教师延聘、教程设置,到教学、实习、展览、校刊、社团的展开,既贡献出合理的育人体系,也呈现出鲜活的办学面貌。而比较武汉美术教育的整体状况而言,其中,前后时局风气的熏陶和关联,地方开明人士对于“美育”责任的承担与投入,让人们见识了这一时期崇实的思想与实践的活跃,以及对于中华文教传统的维护与拓展。
再就中国的抗战美术而论,在武汉所开展的活动,应当是其至关重要的篇章。
抗战初期(1937-1938年)的“大武汉”,汇聚了千余名中华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各艺术门类的“抗敌协会”相继在汉成立,形成了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而美术宣传活动,在全民抗战的自觉意志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组织下,其规模和声势的蓬勃浩大,亦可想而知。然而回望这一段历史,由于此前尚缺乏系统化的检索与归纳,对于其组织实施、人员参与、活动规模、作品形态、在武汉三镇地区的展开、社会性的反响,等等,都只能是某种流于概念化的仿佛的印象。实际上,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意义,恰恰是在于经过更多细节的了解和掌握而进入不同程度的复原,而一个宏观的历史图景,也正是基于细节真实之处的可信、可感方能得以历历的重现。
抗战美术活动的基本史料,不仅可以参阅该时期的文史档案、报刊资讯、各文艺团体的出版物等对于事件的记载,也能通过留存至今的宣传画册、历史照片、美术作品等图像资料的遗存而进行多角度地触摸,由此接近历史图景的具体化认知。而美术活动的本体功能,原本就因诉诸于视觉的形式与内容而具有通俗和直观的特质,因此,大量的漫画和木刻版画,以及巨幅的国画、壁画作品,或刊于报章,或组织展览,或走向街头,以题材广泛的宣传画的方式激扬了民众的精神。
在今天,用于展览的美术作品无几原作的保存,但出版印刷的纸媒中所见画幅,以及老照片中所见的活动场景,却依然丰富且弥足珍贵,由此,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当时代的抗战美术运动的氛围。经过目前的梳理和归纳,这一段历史的景象,如镜鉴一般一一的明朗和清晰了起来。尽管武汉的抗战美术运动历时不过一年,但其留下的记忆和足迹,却至为深沉而雄壮,就美术创作所能起到的社会作用来看,其深刻的历史意义,也远远超出了美术领域自身的实践。
进入新中国时期,湖北美术在国家文艺方针与政策的引领下获得了丰富的成就,并自然形成了相对清晰的发展线索,但就历史梳理的具体工作而言,尽管该时期文献和史料以多样的形态和充分的数量呈现,却同时也在形成精简叙事的方面存在有相当的难度。因为正是由于材料的纷繁,而同时又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与角度所呈现,并由于各种原因所产生事实叙述的出入,因此在材料处理的观念理解与价值判断上就需要先在地建立起相应的标准,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则反映出历史的“当代书写”的制约。
而另一方面,看似丰厚的地方史料与文献留存,在具体探询的过程中却又反映出基础材料的严重匮乏。例如50年代之初,武汉就建设有华中地区最为宏伟的展览场馆——武汉展览馆(即“中苏友好宫”),此后的50、60年代,不仅全国性的美术作品展览多次落脚于此,而苏联等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海外友好国家的艺术作品展览可谓数十次地频繁地来汉交流,也由此可以想见武汉在全国美术格局中的重要位置。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中心展馆所曾经历过的国内、外诸多美术活动,档案性质的原始文件与记录于今均已不存,也就无法详述其状况,只能留待他日详考了。
再者,美术史的建构与美术史文献的梳理,终究也离不开呈现其历史发展序列的美术作品原作的观察。而对于美术作品本身的重视与典藏,在这一时期则缺乏了必要的自觉意识,就国家机构而言,本地博物馆、美术馆未见其制度与实施,就创作者个体而言,也未能有足够的善待和保存。总之,诸多曾经见诸于著录的重要作品的流失,影响了对这一时期美术作品成就的视觉化的感知。
足够明确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主流价值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几乎所有的美术活动,均紧密围绕着各个历史时段的思想与政治运动而展开,并融入整个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洪流,随着历年来的话语主题而跌宕起伏。由此角度来看,尽管地方性的美术活动仍然包含了丰富的内涵与特色,留下诸多足够回味的人物、作品、事迹与掌故,但其总体的艺术思想与创作模式,则仍因趋同而形成主旋律。如就地方性美术中的积淀而言,起始于50年代并持续发展到80年代的“一冶工人版画”、在70年代里声名远播的“黄陂农民泥塑”等等,均在特定形势之下形成创作特色并带有强烈的思想政治印迹。而今,对于这些地方性美术的梳理,通过多种文献方式的综合,也通过口述史料与文本材料的相互印证,那些许许多多生动而鲜活的细节,与当时各种类型的为时代而服务的美术创作相汇合,共同构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宏大叙事。
进入80年代,以改革开放为时代的背景,中国的美术活动回归于艺术本体的反思与实践,通过思想的解放而开拓美术的审美与现实功能,并奠定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基础。
湖北美术的活跃性与创造力,在组织、自觉、自发的多个层面上展开:大型展事的策动、理论争鸣刊物的创办、艺术探索团体的涌现、个体艺术家的突破,等等,作为中国现当代艺术中重要的思潮与现象,均居于这个时代的前列。
然而就由时间所构成的历史维度来看,阶段性成果的迫近,以及非艺术因素的交错,使得文献梳理的工作容易陷入众多材料和人事的迷局,或因平行的铺陈而流于平庸。历史的书写,并非历时性流程的简单纪录,而尤其需要时间和理性的从容考量。在此,时间的概念,意味着沉淀,意味着评价,也意味着判断的确立。
主旋律美术的创作成果,自然是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收获,也让湖北的美术曾获有“美术大省”的称誉。然而在这一时期尤其值得一书的,则是湖北武汉的“新潮美术”运动,并因之而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探索实践中的一个“重镇”。
湖北的美术思潮,并非如一度所误解的非体制艺术,它同样具有着美术机构组织与艺术家群体自发的双重特点,在一个整体的时代氛围里,实践、理论、批评的联动,激发和促进了当代美术在新的思想中的碰撞和成长,并通过艺术家个体的践行而多向地展开。因此,检索湖北的“新潮美术”历程,它既反映为自觉思想的观念过程,同时也反映为视觉形态的实践过程。尽管在全面范围的湖北美术创作中,探索性质的艺术实践并非始终占据主导的地位,但其群体的力量和精神气质却影响深远,并在当下的艺术实践中不断地延伸。
就艺术史的角度综合而论,20世纪的湖北美术,始终应和着时代的沉浮与咏叹,既接受着时代的熏陶,也为时代贡献出独特的成果,经过《百年纵横》美术文献的梳理和回顾,集中显现出了感人的面貌。
处于当代语境之中的文献历史的梳理,不仅是用以解释过去的,更为重要的是指向于未来。艺术史的建构,原本就是文明积累中最富于感念的篇章,其并非满足于记忆的恢复,而是试图进入艺术创造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的探询,并激励人们对于审美化创造人生的向往之心。
现代科学考古把“楚文化”的发掘成果贡献于人们的视野,并使之成为当前荆楚文化发生与发展的远因及其阐释,由此也让湖北的当代艺术实践,在深具崇实精神的同时,也具有了楚地的浪漫传统与理想主义的回味。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的湖北美术,在与时代气运的相互砥砺中,暗合了文脉,收获了底蕴,并向未来敞开进取的空间。
2012年11月于湖北美术学院
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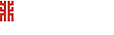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