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漆·赏器·讲礼
张颂仁
漆材是个性鲜明的材质,研究漆材的“艺品”是为了建立漆艺的独立艺术地位。树立“漆品”,在大漆的材质特性和工艺传统内必须要找到发挥性情的品赏角度,即西洋论述所指的审美范畴。从中国的品赏传统来说,诗品与画品铺陈的感知与性情类型,是谈论“漆品”首先须要参照的例案。漆艺立足“艺术”界的困境是漆师受制于器物造型的气质与功能,和受制于“艺术”和“工艺”之分途,以西方现代性理论来说就是无法清楚谈论其本身的独立性。品漆以材质与大漆的工艺传统为依据,把材质层面从器型的载体独立开来,比较容易说明漆艺的特性。
大漆有魅力,引人入胜,这大家都能感受。而作为被品赏的对象,大漆首先面对的是历史悠久的“画品”理论。大漆既然有材质的独特品性,也就有可能发挥某些书画所不擅长表现的感性品质。前人对品漆的理论不多,这里姑且聊辟几目,如“幽”、“贵”与“浑”,以便题点欣赏角度。可是要深入探讨的话,尚须与画品相互推敲。在这里,大概“幽”作为探讨点比较能够突出大漆的性情。
“幽”字描写情景大致皆附于他字,如“幽雅”、“幽致”、“清幽”、“幽寂”、“幽缈”等语,而书画一般不以“幽”作为入品的特类境界。可是,“幽”所联想的情景又的确刻划出诗品画品所崇尚的意境。以司空图《诗品》为例,如“遇之匪深,即之愈希” (“冲淡”)、 “太华夜碧,人闻清钟”(“高古”)所描写的境界,如直接用幽字的“幽人空山,过雨采苹”(“自然”)、“要路愈远,幽行为迟” (“缜密”),都不难在画境中想象。可见“幽”似乎自有意境,可是又不容易被固定为画品的“境界”。再且“幽”字指向黝暗环境,但是绘画在纸绢呈现时,白底黑墨,画面所见皆明白如昼,“幽”字的深邃暗晦情景又一洗而清。描写“幽”境,书画显然有所局限。转而求于漆画,画境比较接近。漆作层层累积,反覆磨洗,于浑沌里沈潜景色,于黝暗处浮现影像,幽境乃不言而喻。历来论画不及于“幽”品, 大概由于纸绢的物质原因,不利于表达黝暗,尤其无法像漆画或油彩堆积层次,更不能使影像从深层底下透现。
“幽”境如能添补书画所不及,还须研究“幽”的境界应该如何界定。这里可能有两条必经的途径。一是重新打开现代人对暗光情境的审美;一是从文化源头重新认识“幽”字义的来源。
现代生活对环境要求的明亮度让我们很难想象电灯发明前的室内生活。文化上来讲,西方人把黑暗与光明对立,而且习惯象征为道德上的罪恶与清明对立。这在心理层面与西方一神教把道德绝对化也是一致的。细菌要绝对消灭,敌人与恶魔一定打下地狱,幽室要光明普照,现在这些观念渐渐成为普世认同。这种对明亮的道德认同,让冥夜、幽微、深邃的神秘感和魅力变为危险、邪恶、鬼魅。这是我们首先应该扭转的观念。其实,暗光情景在传统文化中是富于内容、蕴藏精妙的天地。老子的“知白守黑”、易经的“微显阐幽”,都把阴暗与明亮两种境地平等地看待。可是再追问下去:幽雅恬静,深邃曲折又如何成为审美境界呢?如何成为心与境交融,让心胸渐次开阔的境界?
汉代《说文》谓“幽,隐也。段注:从山,犹隐从阜,取遮蔽之意。”自此“幽”的山林隐蔽意象把高士、隐士、仙道都归到“幽”境之中。可是要达到画品境界的层次,还要达到《淮南子说山训》写的“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谓之幽冥”的高超面貌。这点必须从“幽”的古意追寻。根据中山大学郭静云老师的研究,“幽”成为黑暗义的“黝”字,乃出自汉代观念。她从殷商甲骨文印证,“幽”原属五种基本色调,所指即后来的“青”色,而且“幽”字原来与“玄”字同义(或是同一个字)。“幽”原义指昊天之色,到了周朝,“幽”、“玄”二字分途,“玄”替代为昊天之色,而“幽”转而专指木青色(故此从山),直到“青”字出现才被替代。“幽”之为色,原来乃属天色,后来转而取山林之色,于是郭静云老师认为“幽”色乃兼指昊天高山的“上界”之色。在甲骨文中“幽”字原来多与“黄”字对称,尤其在挑选祭牺毛色时配用于“天幽(玄)地黄”等句。故此而知“幽”色象征上天,交合黄色的地而生养万物,其义深殖华夏宇宙运行观念之中。故此思考后世“幽人”之隐,或应保留“天人”的遗意,应该赋予孕育大地元气之义。“幽”品之境界,应该在画品的“神品”“逸品”等以外另有天地。
“幽”与“玄”的色彩在战国逐渐趋向黝暗,主要原因是昊天之色的光线度本来就很宽,从青天包括到冥天,而汉人把超越日月星辰的“纯天”定在早晚日月两星都不出现的时分,于是光度逐渐接近后代对“幽”和“玄”两字的黝暗定义,(不过此义必须要分别于绝对无明的“黑”色)。从漆艺的立场追寻“幽”的意境,应当参考在早晚不见日和月的“纯天”光度。在此“纯天”境界,漆家自应大有可为。
漆艺的载体历来都以器皿为主,带有“境界”的漆艺就更须要考究器皿的功能和气质。文房与厨具身份有别,礼器与常器不同,阶级观念搁在这里没有办法。器的功能和气质亦必须互相切合才可成就佳器。至于今天艺术圈追求的无功能“艺术物”,对于漆家来说,除非是礼器,否则大可不必。前人言礼,对于今天的艺术界来说,最有意思的启示是礼器相对于日用品的关系,就是说,如何以“艺术”开启日常生活。依今天的说法礼器也是一种“艺术物”,而中国礼器的造型是基于实用品而提炼的,所以器形审美、赏器的基础应该在于实用品,应该从实用品的功能与造型中寻找欣赏器物的原则。
造器者讲究“礼”,就是讲究“物”在世上的位置。《礼记曲礼》篇谓“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家中祭器之用,在于供奉祖宗神灵,也就是给先人准备的实用品,所以要比生人使用的器物更优美庄重。至于古人祭天等礼器,原来由大人天子专用,今天大概不必考虑。《礼记》说要先办祭器,后办养器,这样来说,制造日常使用的器物,也须要带着制做礼器的精神才对。《祭统》谓“不斋则于物无防也,嗜欲无止也。及其将斋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讫其嗜欲,心不苟虑,必依于道。”虽然这里泛指可欲之物,但是对造器者和用器者这是对“艺术物”很好的定义。对于“艺术物”,无论是造物或用物,必须持以敬畏之心,才可以“防邪物”,以致其“心依于道”。换而言之,“艺术物”在世上是为了防止“邪物”和为了正心而做的。
面对产业社会的物质泛滥,和资本社会对工作速度的制度性掌握,漆艺的慢节奏工序可以说是逆行的颠覆。无数层叠髹漆覆盖之下的时间层只能依靠敬畏心的“斋”完成,这些累积的时间层抗衡着不断加速的社会时间,成为养生与养心的“养器”。今天漆艺还是须要回到养心的“养器”才会找到在艺术界中的不移位置,防止嗜欲的“邪物”,并打通漆艺在文明史中的脉络。
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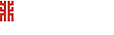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0704号